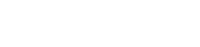于是有了挑起事端的假春桃,有了手握证据的夏荷,有了朝堂之上为左嫣然求情的冷氏。
长公主为什么会知道?自己?的侍女出现了异常?那张被吞掉的纸条上到底写了什么内容?
她一步三?算,是否也将陈秀平算在了其?中?
这个总是唯唯诺诺隐忍不发?的女人,被逼到绝路时?,竟是以?一己?之力,要所有有能之人,都站在左嫣然的背后,为她的未来?抗争,发?声。
“可左嫣然的死活与你何?干?”唐拂衣问,就?连她自己?都未曾发?觉自己?的语气里已经自然而然的带了些悲伤与责备。
“她的死活确实与我无关,但我却觉得任何?人都不应该死得毫无意义。”她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1],却不可无所为,无可得。”
“嫣然姐姐是我重要的人,所以?我想帮她,不是帮她躲过一劫,而是借这个机会,帮她离开这里,一劳永逸,从此天高海阔,再无桎梏。”
唐拂衣张了张嘴,一种名为“迷茫”的情绪一下?子将他的嗓子堵住。她不知该说些什么,她想大?声骂她蠢,骂她活该,骂她疯癫。
她想嘲讽苏道?安,是不是觉得自己?无比高尚,又想质问她,为什么能如此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可以?拯救所有人?
可苏道?安刚刚发?病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又怎么能把自己?这些担心和愤怒,发?泄到一个对世间万物?都抱有善意,同时?也默默承担着这份善意带来?的恶果的女孩身上。
“拂衣,你看吧。其?实我也不是很好的人。我想帮嫣然姐姐是很自私的事情,我让爱我的人如此担心,但我在那个时?候确实想不了太多。”
可若非苏道?安出事,萧祁便不会彻查。揪不出何?氏,对北萧而言,东南战事一败再败,无人知道?后果如何?,对苏家而言,白虎营中的毒瘤不拔除,亦是后患。
苏道?安这一举动是否只?如她所言是出于一己?之私?
唐拂衣不知。
但她还记得当时?小公主一面吐血一面在她手掌心写下?的那个“甘”字。
苏道?安这一举动是否值得?
唐拂衣亦不知。
但至少自私一词,实在是有失偏颇。
“那你自己?呢?”她听到自己?颤抖着地,略有些绝望地声音,“你会死的。”
“我不会的。”苏道?安的声音仿佛此刻安抚心灵的良药,“我生在宫中,有许多爱我,重视我的人,无论多稀有的药材,总会有人尽力为我寻来?。我不爱喝药,也会有人唠唠叨叨。”
“但嫣然姐姐不一样,如果我不帮她的话,她才真的会死掉。”
唐拂衣没有回应,她本能的想要反驳,却无话可说。
分明承受痛苦的人是苏道?安,可软弱的人是她,愤怒的人是她,被安慰的人也是她。
“现在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了。”苏道?安抱着唐拂衣,她似乎是笑着的,声音里带了丝微不可查的甜,“小满和惊蛰都不知道?,如果她们知道?的话,肯定会告诉我娘,所以?你也要帮我保守秘密。”
就?像是一个小姑娘藏了一颗糖,神秘兮兮地告诉自己信任的朋友。
“嗯。”唐拂衣点头的时?候,觉得自己?竟是生出了一丝十分微妙地责任感?。
她要帮小姑娘一起藏好这颗糖,不能让这颗糖被“坏人”拿走;她也要保护好她,让这颗糖的存在永远都有意义。
她扬起头,月亮仍是那个月亮,没有半点脏污。
而霉烂丛生的那个,不过倒映在肮脏地池水中的一汪幻影。
“拂衣。”
“嗯。”
”我的灯灭了。”
苏道?安的声音几乎没入黑暗,她似乎是笑了一声,唐拂衣听清了那最后一句话:
“为我点灯吧。”
-
“知道?了,你出去吧。”
衣着贵气的妇人坐在桌前轻轻挥了挥手,跪在她身前的女人站起来?,沉默着转过身。
窗边的烛火摇曳,映的横亘在她面上的那道?疤痕触目惊心。
陈秀平侧目看着桌上的那封信,皱巴巴的封面大?半都被鲜血浸染,暗红的血色中,显出四?个大?字:
阿芙亲启。
良久,她才抬手拿起那封信,小心翼翼地将它拆开。
“吾友阿芙,见字如面。
只?是想来?你如今应该并不想见我,便以?此书信,与你做最后的话别。
自两年前飞桁身死,我与爱女嫣然被迫入宫,我二人便再未见过。遥记少年时?,你我一同策马踏花,好不痛快。后我嫁与飞桁,你却扬言自己?不愿嫁与匹夫草草余生。
我原还担心以?你的性子,虽能成就?一番功业,却恐怕是要孤老终生。只?是未想到半路杀出个陈咬金,虽有曲折,却还是抱的美人归。
苏家是世代功勋,苏栋人品贵重,颇具才干,又深爱着你,阿芙能嫁与他,也算是好事多磨。
我知此事想来?是瞒不过你,误伤到涉川并非我本意,但我要为嫣然筹谋,如此情景下?,只?能出此下?策。
我自知我罪无可恕,亦无意为自己?辩解,只?得以?死谢罪。
此枚戒指是我的夫君左飞桁留给我的护身之物?,如今赠予你,亦赠予苏家,望你收下?,日后若有颠覆,想必能有所助益。
宣明二年春,萧黎绝笔。”
烛火摇曳,宣纸上的墨迹忽明忽暗,娟秀的小字如豆蔻少女,踮起脚尖在血色晕开的花儿?上翩翩起舞。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2]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3]。
陈秀平的眼中有泪,目光游移,落到桌上那一枚镶了翡翠的金色扳指上。
翡翠上刻了一个“左”字,近半寸的厚度,很明显并非是日常佩戴的首饰。
她盯着那戒指看了一会儿?,将信放到了蜡烛之上。火焰如舌,舔过脆弱浅薄地宣纸,很快最后一丝痕迹也在空气中消失殆尽。
陈秀平眼神淡漠疏离,她将那扳指拿起,放进了房中的暗格。
-
受了一夜的凉风,苏道?安还是没能逃过一病。
幸运的是这一场风寒来?势不凶,在床上躺着被葛柒柒念叨了两日,苏道?安便已能下?床走动,又喝了两天药,看着便又是活蹦乱跳了。
这一日天气晴好,苏道?安一大?早便梳妆打?扮出了宫去。
小满总算是能逮到一个机会,喊了几个人一起将寝殿内外仔仔细细地打?扫了一遍。所有窗子都被开到最大?,金灿灿地阳光几乎洒满房间地每个角落,轻风穿堂而过,将屋内弥漫着地药味和病气全部一扫而空。
唐拂衣抱着一盏刚修好地宫灯,踏进寝殿地那一刻,竟是豁然开朗之感?。
她来?千灯宫将近两个月了,这还是头一次见床边地窗户如此般开到最大?,几乎都已经看不见窗扇,木质地窗框框出后院地景象。
晴云轻荡,花山层叠,细石清俊,如在画中。
竟已是初春了。
唐拂衣看着山下?地石头中已经冒了绿芽地迎春,有些出神。
“欸,拂衣。”小满从一个柜子后头抬起头,“这灯你修好啦?”
她已经忙活地差不多了,见到唐拂衣进来?面露惊喜,放下?抹布快步跑过来?,从唐拂衣地手中接过那盏金银相间地灯,举高了些细细端详起来?。
“还真是一点看不出坏过啊。”她忍不住叹道?,看向唐拂衣地目光里满是钦佩。
自从苏道?安发?病那晚之后,唐拂衣似乎开朗了许多,小满一直觉得此事自己?也有责任,对唐拂衣的行为原本也没有抱有太大?的不满,再加上苏道?安本人也并不追究。如此一来?,她对唐拂衣的改变倒也十分开心。
“只?是恰好小时?候学过一些。”唐拂衣笑道?,“公主今日起的这么早,是去了哪儿??”
“去给太后请安了。”小满将灯放到书桌上,又回到柜子边拿起了抹布,“太后最疼我们公主了,但她上了年纪,也怕过了病气,公主也好久没去太后宫里了。”
“如此。”唐拂衣点头,正准备回身离开,余光却瞥见了窗外一人正蹲在地上侍弄花草。
“小满。”她唤了一声。
“怎么了?”小满的声音从柜子后边传过来?,显得有些闷闷地。
“谁陪公主一起去给太后请安?”她问。
“惊蛰啊。”小满答。
“……”唐拂衣看着院子里那个腰挂轻刀的女人,“你确定……是惊蛰陪公主一起去得的么?”
[1]司马迁《报任安书》
[2]苏轼《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3]刘过《唐多令》
长公主为什么会知道?自己?的侍女出现了异常?那张被吞掉的纸条上到底写了什么内容?
她一步三?算,是否也将陈秀平算在了其?中?
这个总是唯唯诺诺隐忍不发?的女人,被逼到绝路时?,竟是以?一己?之力,要所有有能之人,都站在左嫣然的背后,为她的未来?抗争,发?声。
“可左嫣然的死活与你何?干?”唐拂衣问,就?连她自己?都未曾发?觉自己?的语气里已经自然而然的带了些悲伤与责备。
“她的死活确实与我无关,但我却觉得任何?人都不应该死得毫无意义。”她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1],却不可无所为,无可得。”
“嫣然姐姐是我重要的人,所以?我想帮她,不是帮她躲过一劫,而是借这个机会,帮她离开这里,一劳永逸,从此天高海阔,再无桎梏。”
唐拂衣张了张嘴,一种名为“迷茫”的情绪一下?子将他的嗓子堵住。她不知该说些什么,她想大?声骂她蠢,骂她活该,骂她疯癫。
她想嘲讽苏道?安,是不是觉得自己?无比高尚,又想质问她,为什么能如此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可以?拯救所有人?
可苏道?安刚刚发?病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又怎么能把自己?这些担心和愤怒,发?泄到一个对世间万物?都抱有善意,同时?也默默承担着这份善意带来?的恶果的女孩身上。
“拂衣,你看吧。其?实我也不是很好的人。我想帮嫣然姐姐是很自私的事情,我让爱我的人如此担心,但我在那个时?候确实想不了太多。”
可若非苏道?安出事,萧祁便不会彻查。揪不出何?氏,对北萧而言,东南战事一败再败,无人知道?后果如何?,对苏家而言,白虎营中的毒瘤不拔除,亦是后患。
苏道?安这一举动是否只?如她所言是出于一己?之私?
唐拂衣不知。
但她还记得当时?小公主一面吐血一面在她手掌心写下?的那个“甘”字。
苏道?安这一举动是否值得?
唐拂衣亦不知。
但至少自私一词,实在是有失偏颇。
“那你自己?呢?”她听到自己?颤抖着地,略有些绝望地声音,“你会死的。”
“我不会的。”苏道?安的声音仿佛此刻安抚心灵的良药,“我生在宫中,有许多爱我,重视我的人,无论多稀有的药材,总会有人尽力为我寻来?。我不爱喝药,也会有人唠唠叨叨。”
“但嫣然姐姐不一样,如果我不帮她的话,她才真的会死掉。”
唐拂衣没有回应,她本能的想要反驳,却无话可说。
分明承受痛苦的人是苏道?安,可软弱的人是她,愤怒的人是她,被安慰的人也是她。
“现在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了。”苏道?安抱着唐拂衣,她似乎是笑着的,声音里带了丝微不可查的甜,“小满和惊蛰都不知道?,如果她们知道?的话,肯定会告诉我娘,所以?你也要帮我保守秘密。”
就?像是一个小姑娘藏了一颗糖,神秘兮兮地告诉自己信任的朋友。
“嗯。”唐拂衣点头的时?候,觉得自己?竟是生出了一丝十分微妙地责任感?。
她要帮小姑娘一起藏好这颗糖,不能让这颗糖被“坏人”拿走;她也要保护好她,让这颗糖的存在永远都有意义。
她扬起头,月亮仍是那个月亮,没有半点脏污。
而霉烂丛生的那个,不过倒映在肮脏地池水中的一汪幻影。
“拂衣。”
“嗯。”
”我的灯灭了。”
苏道?安的声音几乎没入黑暗,她似乎是笑了一声,唐拂衣听清了那最后一句话:
“为我点灯吧。”
-
“知道?了,你出去吧。”
衣着贵气的妇人坐在桌前轻轻挥了挥手,跪在她身前的女人站起来?,沉默着转过身。
窗边的烛火摇曳,映的横亘在她面上的那道?疤痕触目惊心。
陈秀平侧目看着桌上的那封信,皱巴巴的封面大?半都被鲜血浸染,暗红的血色中,显出四?个大?字:
阿芙亲启。
良久,她才抬手拿起那封信,小心翼翼地将它拆开。
“吾友阿芙,见字如面。
只?是想来?你如今应该并不想见我,便以?此书信,与你做最后的话别。
自两年前飞桁身死,我与爱女嫣然被迫入宫,我二人便再未见过。遥记少年时?,你我一同策马踏花,好不痛快。后我嫁与飞桁,你却扬言自己?不愿嫁与匹夫草草余生。
我原还担心以?你的性子,虽能成就?一番功业,却恐怕是要孤老终生。只?是未想到半路杀出个陈咬金,虽有曲折,却还是抱的美人归。
苏家是世代功勋,苏栋人品贵重,颇具才干,又深爱着你,阿芙能嫁与他,也算是好事多磨。
我知此事想来?是瞒不过你,误伤到涉川并非我本意,但我要为嫣然筹谋,如此情景下?,只?能出此下?策。
我自知我罪无可恕,亦无意为自己?辩解,只?得以?死谢罪。
此枚戒指是我的夫君左飞桁留给我的护身之物?,如今赠予你,亦赠予苏家,望你收下?,日后若有颠覆,想必能有所助益。
宣明二年春,萧黎绝笔。”
烛火摇曳,宣纸上的墨迹忽明忽暗,娟秀的小字如豆蔻少女,踮起脚尖在血色晕开的花儿?上翩翩起舞。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2]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3]。
陈秀平的眼中有泪,目光游移,落到桌上那一枚镶了翡翠的金色扳指上。
翡翠上刻了一个“左”字,近半寸的厚度,很明显并非是日常佩戴的首饰。
她盯着那戒指看了一会儿?,将信放到了蜡烛之上。火焰如舌,舔过脆弱浅薄地宣纸,很快最后一丝痕迹也在空气中消失殆尽。
陈秀平眼神淡漠疏离,她将那扳指拿起,放进了房中的暗格。
-
受了一夜的凉风,苏道?安还是没能逃过一病。
幸运的是这一场风寒来?势不凶,在床上躺着被葛柒柒念叨了两日,苏道?安便已能下?床走动,又喝了两天药,看着便又是活蹦乱跳了。
这一日天气晴好,苏道?安一大?早便梳妆打?扮出了宫去。
小满总算是能逮到一个机会,喊了几个人一起将寝殿内外仔仔细细地打?扫了一遍。所有窗子都被开到最大?,金灿灿地阳光几乎洒满房间地每个角落,轻风穿堂而过,将屋内弥漫着地药味和病气全部一扫而空。
唐拂衣抱着一盏刚修好地宫灯,踏进寝殿地那一刻,竟是豁然开朗之感?。
她来?千灯宫将近两个月了,这还是头一次见床边地窗户如此般开到最大?,几乎都已经看不见窗扇,木质地窗框框出后院地景象。
晴云轻荡,花山层叠,细石清俊,如在画中。
竟已是初春了。
唐拂衣看着山下?地石头中已经冒了绿芽地迎春,有些出神。
“欸,拂衣。”小满从一个柜子后头抬起头,“这灯你修好啦?”
她已经忙活地差不多了,见到唐拂衣进来?面露惊喜,放下?抹布快步跑过来?,从唐拂衣地手中接过那盏金银相间地灯,举高了些细细端详起来?。
“还真是一点看不出坏过啊。”她忍不住叹道?,看向唐拂衣地目光里满是钦佩。
自从苏道?安发?病那晚之后,唐拂衣似乎开朗了许多,小满一直觉得此事自己?也有责任,对唐拂衣的行为原本也没有抱有太大?的不满,再加上苏道?安本人也并不追究。如此一来?,她对唐拂衣的改变倒也十分开心。
“只?是恰好小时?候学过一些。”唐拂衣笑道?,“公主今日起的这么早,是去了哪儿??”
“去给太后请安了。”小满将灯放到书桌上,又回到柜子边拿起了抹布,“太后最疼我们公主了,但她上了年纪,也怕过了病气,公主也好久没去太后宫里了。”
“如此。”唐拂衣点头,正准备回身离开,余光却瞥见了窗外一人正蹲在地上侍弄花草。
“小满。”她唤了一声。
“怎么了?”小满的声音从柜子后边传过来?,显得有些闷闷地。
“谁陪公主一起去给太后请安?”她问。
“惊蛰啊。”小满答。
“……”唐拂衣看着院子里那个腰挂轻刀的女人,“你确定……是惊蛰陪公主一起去得的么?”
[1]司马迁《报任安书》
[2]苏轼《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3]刘过《唐多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