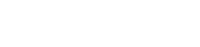第60章
陈盼也在流泪,喃喃道,“这时候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临死了知道对不起我了,她早干什么去了?”
柜子里的寿衣被拿出来,套在了张珍瘦小的身体上,寿衣还是大了,她估计也没想到自己会瘦成这个样子。
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过了很久,陈盼说:“你给亲戚打电话吧。”
陈沂机械地调出电话本,像是机器人一样通知所有的亲戚,其他人的宽慰和痛哭,他都觉得好远,甚至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就恍然到了第二天。
一群亲戚一大早上敲响了门,设灵堂,拉棺材,院子里时隔这么多年又停了一口棺材,停在陈沂打扫了好多天整理的井井有条的院子里,那时候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打扫是做这个作用,那一刻他甚至怨恨自己的勤劳。
亲戚来了一上午,下午就散去,今天是除夕。
晚上,棺材停在院子里,灵堂的照片也印了上去。
年夜饭,他们什么都没准备,只好把昨天拌好的饺子馅拿出来,铺开桌子开始包饺子。
饺子下锅,陈沂看着锅里泛起的白气发呆,有人开始放鞭炮,一个接着一个,他想起来堆在角落的春联和福气,本该是在除夕当天贴上的,现在都化作了无用之物。外面那么喜庆,这个家里这样空寂。
饺子上桌,他想起来昨天还和张珍说要多吃几个,眼泪落在碗里,他根本尝不出饺子的味道。那饺子谁也没吃,又完完整整地放到了厨房。
大年初一,晴天,棺材摆在那,村里的人嫌不吉利,路过他家门口都要绕路。按照习俗大年初一不能出殡,棺材就只好在院子里摆着,陈沂去买了烧纸,花圈,一系列需要准备的东西,他发现他在这时候居然这样熟练,就像天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情。
大年初二,一众亲戚在一大早又过来,按照习俗,陈沂花钱请了最好的阴阳先,各种东西也按最好的来,即便知道这些毫无用处。他看见一队人带着乐器敲敲打打,后来是几个他不认识的女人趴在棺材旁边哭。
她们见过太多去世的人了,哭得却比真正失去亲人的人看起来悲伤。
一通仪式结束已经是傍晚,有车开过来,现在已经不需要人气来挖坑和搬棺材,坑已经在地里挖好,车上有升降的仪器。
深红的棺材被一大把一大把冻土覆盖,寒风吹干脸上的泪痕,陈沂觉得脸颊像刀刮一样疼。
他恍惚地回到家,院子里空空的,人群来了又散去,只剩下地上泛黄的纸钱,陈盼在扫地,陈沂接过扫把,麻木地打扫。
入了夜,格外冷。
陈沂骤然想起来这几天晏崧没有联系他,连晚上的电话也没有再打过。
他翻出手机,看见消息停留在几天前。
想了想,陈沂又把手机放下。
睁眼到天亮,陈沂发现自己的胡子已经冒出来一茬,车票是几天后的,他还需要在这里待几天,荒凉的日子,他一宿一宿的睡不着,拜年短信他一个都没回,家里有丧事要守丧避吉。
头七那天,陈沂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去墓碑前烧纸,他还是无法想象一个活的人为什么此时此刻在面前冰冷的土壤里。
晚上回去他终于将将睡了一会儿,却又开始做梦。
他梦见小时候的午后,阳光洒在阳台上,一朵朵花被人搬到了室外,陈盼拿着剪子在剪枝条,陈沂拿着凳子坐在阳台下,和陈盼一起,手里拿着一个绿豆冰棍,他正在换牙,不敢咬,只能一口一口舔,说话也漏风。
张珍的身影那样清晰,陈沂却看不清楚她的脸,只知道她变成了年轻时候的样子,笑得慈爱。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大概是学校里的成绩,张珍笑着说:“好好学习,长大一定会有出息的!”
小小的陈沂呲着漏风的牙笑了,可下一刻张珍变了样,瘦成了一把骨头,说:“陈沂,你要传宗接代,你不能喜欢男人,你不是同性恋!”
陈沂骤然惊醒,全身都是冷汗。
他找出自己的药,来不及分辨什么就吞进胃里,梦里的场景不停在他脑海里闪现,他的焦虑发作,全身都不受控制得发抖。
陈沂深呼吸,逼自己冷静。他拿出手机,想立刻听见某个人的声音,可打开聊天框那一刻他却僵住了。
遍地的拜年短信里,晏崧的上一条消息还停留在年前。
他想打电话过去,却止住自己的手,现在不是个合时宜的时间。
他只好打字,他的手太抖了,几个字都要碰上半天。
他说:【新年快乐】
明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说这样的话,他还是发送了出去。
隔了很久,也许两分钟,也许两年。
陈沂终于收到了回信,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他咬着下唇接通,听见晏崧那热闹的嘈杂,和他这里仿佛是两个世界。
晏崧说:“想起来我了?”
陈沂指甲嵌进了掌心,没有心力分析他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哑声说:“对不起。”
晏崧停顿了一瞬,似乎觉得他这声音有些可怜,妥协道:“新年快乐。”
他开了视频,陈沂看见他在海边,朝思暮想地脸一晃而过,岸边都是穿着泳衣的人。
晏崧说:“请你看烟花。”
五颜六色的烟花在他这话落下的时间瞬间亮起,照亮了整个天际。
陈沂的眼泪再也压制不住,只是烟花的声音太大了,晏崧听不见他的哭声。
烟花持续了十来分钟,电话亮着,陈沂哭得什么都没看清楚。
烟花结束,晏崧听见陈沂轻轻的声音在失真的电话里,陈沂说:“很漂亮,谢谢你。”
第54章 第三者
临走前一天,还没有到元宵节。
这都是两个人在家里的最后一夜,月明星稀,还没到十五月亮已经很圆了。
屋里灯有年份,是橙黄色的,还能亮已经很不容易,陈沂和陈盼两个人都在收拾行李,其实他们都没有什么东西,比行李更少的是话。
空气过于沉默,陈沂一阵阵发冷,他问:“姐,你打算去哪里?”
陈盼沉默一瞬,“去南方吧,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
她把行李装好,“她死了,我也算解脱了。现在没什么可牵挂的,折腾这么多年,我谁也不欠了。”
陈沂哑声说:“这些年辛苦你了,姐。”
陈盼无所谓地笑笑,看他一眼,似乎有话要说,但又咽了回去,片刻后,她问,“你谈对象了?怎么不带回来看看,她这些年一直想让你谈一个,不知道该多高兴。”
陈沂沉默了,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陈盼抬起头,“怎么?难道你骗她的?”
“没有。”陈沂下意识摇摇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但他现在也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我……我其实不喜欢女孩。”
瞒了这么多年的话吐出来,陈沂心里竟然感受到一丝畅快,可他没预料到陈盼的反应。
陈盼本来在往包里装杯子,他这话一落下,陈盼手里的杯子直接落在了地上,滴溜溜滚到陈沂脚下。
“什么?”陈盼音调拔高,“你再说一遍!”
“我是同性恋。”陈沂涩声说,“很多年了。”
“不对,不对。”陈盼猛然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你怎么能是同性恋呢?”
她眼睛有些红了,见陈沂的反应便知道这事儿不是开玩笑。她问:“所以你天天在和一个男的打电话?”
陈沂迟疑地点了点头。
陈盼眉头紧皱,凝视着自己的弟弟,片刻后说:“你真恶心。”
陈沂全身一冷,一道寒意仿佛瞬间浸透了五脏六腑,那一瞬间他甚至察觉到了耳鸣,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尖锐,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姐姐。
“恶心”这两个字让他有了应激反应,上一次出自晏崧之口,而这一次来自他的亲人。这话像直直往他心脏里头刺。
陈盼走到他跟前,喃喃道:“你怎么会喜欢男人?你怎么会是同性恋?”
她的眼睛赤红,因为张珍去世还没有消肿,“她一辈子都搭在你身上,我这半辈子也搭在你身上,你怎么能是同性恋?”
陈沂控制不住发抖,哑声道:“对不起,对不起。”
他知道,张珍这一辈子是为了谁,陈盼和那样一个人结婚受益的是什么,如果可以选,他宁愿什么都不要,不念这么多年书,不让所有人用自己的牺牲来成全他。他知道自己足够无耻,他受了这么多好处,最后却只能吐出这徒劳的三个字。
陈盼抹了一把脸,“改不好了,是吗?”
陈沂沉默着摇了摇头。
“全世界都在和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啊。”陈盼笑了一声,笑意不达眼底,眼泪却流了出来。她想起来结婚前那个晚上,张珍告诉她以后要孝顺公婆,要好好伺候丈夫,她那么怕,怕自己不熟悉的丈夫和父亲一样,是个酒鬼,是个暴力狂。
柜子里的寿衣被拿出来,套在了张珍瘦小的身体上,寿衣还是大了,她估计也没想到自己会瘦成这个样子。
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过了很久,陈盼说:“你给亲戚打电话吧。”
陈沂机械地调出电话本,像是机器人一样通知所有的亲戚,其他人的宽慰和痛哭,他都觉得好远,甚至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就恍然到了第二天。
一群亲戚一大早上敲响了门,设灵堂,拉棺材,院子里时隔这么多年又停了一口棺材,停在陈沂打扫了好多天整理的井井有条的院子里,那时候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打扫是做这个作用,那一刻他甚至怨恨自己的勤劳。
亲戚来了一上午,下午就散去,今天是除夕。
晚上,棺材停在院子里,灵堂的照片也印了上去。
年夜饭,他们什么都没准备,只好把昨天拌好的饺子馅拿出来,铺开桌子开始包饺子。
饺子下锅,陈沂看着锅里泛起的白气发呆,有人开始放鞭炮,一个接着一个,他想起来堆在角落的春联和福气,本该是在除夕当天贴上的,现在都化作了无用之物。外面那么喜庆,这个家里这样空寂。
饺子上桌,他想起来昨天还和张珍说要多吃几个,眼泪落在碗里,他根本尝不出饺子的味道。那饺子谁也没吃,又完完整整地放到了厨房。
大年初一,晴天,棺材摆在那,村里的人嫌不吉利,路过他家门口都要绕路。按照习俗大年初一不能出殡,棺材就只好在院子里摆着,陈沂去买了烧纸,花圈,一系列需要准备的东西,他发现他在这时候居然这样熟练,就像天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情。
大年初二,一众亲戚在一大早又过来,按照习俗,陈沂花钱请了最好的阴阳先,各种东西也按最好的来,即便知道这些毫无用处。他看见一队人带着乐器敲敲打打,后来是几个他不认识的女人趴在棺材旁边哭。
她们见过太多去世的人了,哭得却比真正失去亲人的人看起来悲伤。
一通仪式结束已经是傍晚,有车开过来,现在已经不需要人气来挖坑和搬棺材,坑已经在地里挖好,车上有升降的仪器。
深红的棺材被一大把一大把冻土覆盖,寒风吹干脸上的泪痕,陈沂觉得脸颊像刀刮一样疼。
他恍惚地回到家,院子里空空的,人群来了又散去,只剩下地上泛黄的纸钱,陈盼在扫地,陈沂接过扫把,麻木地打扫。
入了夜,格外冷。
陈沂骤然想起来这几天晏崧没有联系他,连晚上的电话也没有再打过。
他翻出手机,看见消息停留在几天前。
想了想,陈沂又把手机放下。
睁眼到天亮,陈沂发现自己的胡子已经冒出来一茬,车票是几天后的,他还需要在这里待几天,荒凉的日子,他一宿一宿的睡不着,拜年短信他一个都没回,家里有丧事要守丧避吉。
头七那天,陈沂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去墓碑前烧纸,他还是无法想象一个活的人为什么此时此刻在面前冰冷的土壤里。
晚上回去他终于将将睡了一会儿,却又开始做梦。
他梦见小时候的午后,阳光洒在阳台上,一朵朵花被人搬到了室外,陈盼拿着剪子在剪枝条,陈沂拿着凳子坐在阳台下,和陈盼一起,手里拿着一个绿豆冰棍,他正在换牙,不敢咬,只能一口一口舔,说话也漏风。
张珍的身影那样清晰,陈沂却看不清楚她的脸,只知道她变成了年轻时候的样子,笑得慈爱。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大概是学校里的成绩,张珍笑着说:“好好学习,长大一定会有出息的!”
小小的陈沂呲着漏风的牙笑了,可下一刻张珍变了样,瘦成了一把骨头,说:“陈沂,你要传宗接代,你不能喜欢男人,你不是同性恋!”
陈沂骤然惊醒,全身都是冷汗。
他找出自己的药,来不及分辨什么就吞进胃里,梦里的场景不停在他脑海里闪现,他的焦虑发作,全身都不受控制得发抖。
陈沂深呼吸,逼自己冷静。他拿出手机,想立刻听见某个人的声音,可打开聊天框那一刻他却僵住了。
遍地的拜年短信里,晏崧的上一条消息还停留在年前。
他想打电话过去,却止住自己的手,现在不是个合时宜的时间。
他只好打字,他的手太抖了,几个字都要碰上半天。
他说:【新年快乐】
明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说这样的话,他还是发送了出去。
隔了很久,也许两分钟,也许两年。
陈沂终于收到了回信,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他咬着下唇接通,听见晏崧那热闹的嘈杂,和他这里仿佛是两个世界。
晏崧说:“想起来我了?”
陈沂指甲嵌进了掌心,没有心力分析他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哑声说:“对不起。”
晏崧停顿了一瞬,似乎觉得他这声音有些可怜,妥协道:“新年快乐。”
他开了视频,陈沂看见他在海边,朝思暮想地脸一晃而过,岸边都是穿着泳衣的人。
晏崧说:“请你看烟花。”
五颜六色的烟花在他这话落下的时间瞬间亮起,照亮了整个天际。
陈沂的眼泪再也压制不住,只是烟花的声音太大了,晏崧听不见他的哭声。
烟花持续了十来分钟,电话亮着,陈沂哭得什么都没看清楚。
烟花结束,晏崧听见陈沂轻轻的声音在失真的电话里,陈沂说:“很漂亮,谢谢你。”
第54章 第三者
临走前一天,还没有到元宵节。
这都是两个人在家里的最后一夜,月明星稀,还没到十五月亮已经很圆了。
屋里灯有年份,是橙黄色的,还能亮已经很不容易,陈沂和陈盼两个人都在收拾行李,其实他们都没有什么东西,比行李更少的是话。
空气过于沉默,陈沂一阵阵发冷,他问:“姐,你打算去哪里?”
陈盼沉默一瞬,“去南方吧,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
她把行李装好,“她死了,我也算解脱了。现在没什么可牵挂的,折腾这么多年,我谁也不欠了。”
陈沂哑声说:“这些年辛苦你了,姐。”
陈盼无所谓地笑笑,看他一眼,似乎有话要说,但又咽了回去,片刻后,她问,“你谈对象了?怎么不带回来看看,她这些年一直想让你谈一个,不知道该多高兴。”
陈沂沉默了,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陈盼抬起头,“怎么?难道你骗她的?”
“没有。”陈沂下意识摇摇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但他现在也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我……我其实不喜欢女孩。”
瞒了这么多年的话吐出来,陈沂心里竟然感受到一丝畅快,可他没预料到陈盼的反应。
陈盼本来在往包里装杯子,他这话一落下,陈盼手里的杯子直接落在了地上,滴溜溜滚到陈沂脚下。
“什么?”陈盼音调拔高,“你再说一遍!”
“我是同性恋。”陈沂涩声说,“很多年了。”
“不对,不对。”陈盼猛然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你怎么能是同性恋呢?”
她眼睛有些红了,见陈沂的反应便知道这事儿不是开玩笑。她问:“所以你天天在和一个男的打电话?”
陈沂迟疑地点了点头。
陈盼眉头紧皱,凝视着自己的弟弟,片刻后说:“你真恶心。”
陈沂全身一冷,一道寒意仿佛瞬间浸透了五脏六腑,那一瞬间他甚至察觉到了耳鸣,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尖锐,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姐姐。
“恶心”这两个字让他有了应激反应,上一次出自晏崧之口,而这一次来自他的亲人。这话像直直往他心脏里头刺。
陈盼走到他跟前,喃喃道:“你怎么会喜欢男人?你怎么会是同性恋?”
她的眼睛赤红,因为张珍去世还没有消肿,“她一辈子都搭在你身上,我这半辈子也搭在你身上,你怎么能是同性恋?”
陈沂控制不住发抖,哑声道:“对不起,对不起。”
他知道,张珍这一辈子是为了谁,陈盼和那样一个人结婚受益的是什么,如果可以选,他宁愿什么都不要,不念这么多年书,不让所有人用自己的牺牲来成全他。他知道自己足够无耻,他受了这么多好处,最后却只能吐出这徒劳的三个字。
陈盼抹了一把脸,“改不好了,是吗?”
陈沂沉默着摇了摇头。
“全世界都在和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啊。”陈盼笑了一声,笑意不达眼底,眼泪却流了出来。她想起来结婚前那个晚上,张珍告诉她以后要孝顺公婆,要好好伺候丈夫,她那么怕,怕自己不熟悉的丈夫和父亲一样,是个酒鬼,是个暴力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