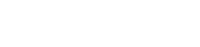第59章
“嗯。”
空气陷入沉静,片刻后陈沂听到有小孩子的声音,不止一个,争着吵着喊哥哥,要晏崧带他们去玩。
晏崧的声音无奈又温柔,说,“一会儿就过去。”
小孩子好奇,问:“在跟谁打电话,是不是女朋友啊?”
“不是。”晏崧否认。
“那就是男朋友咯!”
晏崧走远了,声音越来越小,陈沂的心脏倏地抓紧,他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些什么,可他这里实在太静了,即便那么远他还是听见了晏崧的回答,“肯定不是,你们跟谁学的这些东西?小小年纪不学好!”
另一个小孩的声音传过来,“就是就是,哥哥这么喜欢和我们玩,怎么会是同性恋?”
晏崧不知道孩子的逻辑是什么来的,觉得自己跟小孩实在说不通,无奈地笑了笑。
陈沂苦笑一声,恨自己早知道结果还抱有期待。他把电话挂了,刚才所有想宣之于口的难过也都咽回到了肚子里,那些多余的感动轻轻一戳就碎了,他并没有什么立场要晏崧的安慰和原谅,这几句话彻底点醒了他。
不久之后晏崧电话打了又打了过来,问陈沂为什么挂断电话。
陈沂回:“还以为你在忙。”
晏崧难得解释,“出来吃饭,亲戚家的孩子总是缠着我。”
陈沂牵强地笑笑,声音上听不出奇怪,“你很招小孩子喜欢呢。”
晏崧皱了皱眉,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又从陈沂的语气听不出来什么问题。他顺着陈沂的话开口,不自觉透露出些真实情绪,“看起来和气些而已,总不能说烦。”
陈沂内心一震,不知道该回些什么,怕自己露出端倪,说:“我要睡了。”
晏崧知道他舟车劳顿,大发慈悲:“行,电话不要挂。”
手机亮了一夜,陈沂不知道这算什么。
他看着外面的雪花由小变大,空气越来越冷,从前到现在的日子像是走马灯。他又不自觉地流泪,不发出声音的流泪他同样习惯,即便打了一晚上的电话晏崧也没有发现奇怪。
手机没电的时候电话挂断,陈沂听见了电话里传来的平稳的呼吸。
他也闭上眼睛,发现睁眼和闭眼竟然没有区别,同样看不到明天。
第53章 新年…快乐
雪下了一夜,陈沂被阳光晒醒,推开门遍地都是雪白的。不远处有烟囱在冒烟,村里的日子谁家起床谁家做饭只需要看这个就清清楚楚。
陈沂小时候只需要看自己家里的烟囱有没有烟就知道是不是该回家吃饭。但是现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即便快要过年,燃起来的烟囱也只有寥寥几个。
张珍当时说要回来,便是想念这里年轻时候跟她一起聊家常,一起外出打工的朋友,没想到回来了,村里的人倒是都走了。
陈沂先去捡柴,把火点燃烧热室内,才从满是灰尘的库房里找出两把了锈的铁锹。
新雪下压着积雪,下面的积雪是化了又冻上的,格外难铲。陈沂长时间不运动,没什么力气,动了两下就出了点虚汗。他不知不觉产了一上午,直到从房子门口到院子门口铲出一条可以走的通路,陈沂的手已经被冻的通红。
中午吃过饭他又去铲,投入在体力劳动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用想,他终于看见了积雪下压着的从砖缝里长出来的草,枯萎的叶子下,根却带着一点绿,陈沂把几颗连品种都称不上的杂草移栽到了阳台上的花盆里,妄图从这里面看到一点机。
张珍醒来的时候看见了阳台上的植物,笑话陈沂天真,这草早就被冻死了,怎么可能再长起来。她像草叶子一样枯黄的手覆盖在陈沂手上,说:“要长起来也是从籽开始长,这棵植物的寿数就到这了。”
陈沂摇摇头,执拗道:“不会的,屋里这么暖和,它会长起来的。”
还真如他所说,这草在栽进去的第三天,盆里真长出来点嫩芽。张珍的精神这些天也好了很多,陈盼说这是因为儿子回来了心里高兴。
陈沂却觉得是因为这棵草,他居然把希望寄托在一棵草上。
院子里越来越干净,陈沂拿着推车一车一车把积雪运出去,院子里开始井井有条,天气好的时候他把张珍放在轮椅上推出去晒太阳,晴天的时候不那么冷,房檐下化得都是水,陈沂不敢让人在外面太长时间。
白天体力劳动太多,晚上陈沂会接到晏崧的电话,聊不上几句,陈沂的活实在单调,晏崧的活他也没有立场探究,他只能听见电话里存在的呼吸声,很多次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连通着的电话很多次把他拉回现实。
陈沂知道现在不是晏崧需要自己,而是他需要晏崧。
他希望日子也可以像这一刻一样停止,张珍的精神越来越好,白天时候可以说一些年轻时候的事情,陈沂问她,不恨陈宏发吗?
张珍浑浊的眼睛看得很远,但眼里却是那么平静,她说:“都过去了。”
人死如灯灭,是都过去了。
陈沂觉得那样的日子也离自己很远很远,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情绪可以从身体里抽离出来,整个人都是恍惚的,把希望和执念寄托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事物上,有时候是院子里的积雪,有时候是阳台上的草。
离除夕越来越近,张珍的精神骤然变差,连话都说不完整。
陈沂想起来很多小时候的传闻,说年纪大的老人如果撑过冬天就可以再活下去一年,说人心里的一桩心事放下彻底没念想的时候会彻底腐败下去。他已经不祈求撑过冬天,他只想至少过了这个除夕。
从腊八到小年,那颗草变软,变潮,最后一点绿被吞噬,陈沂浇了太多水,一颗野草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希望,死得不能再死,手按上去流出来的都是脓。
它没有挺到除夕,就彻底和泥土化作一起。
陈沂开始在陈盼跟前守夜,和陈盼轮着,隔一会儿探一探张珍的呼吸。他看张珍合上的满是皱纹的眼皮,头上的帽子快能盖住整个脑袋。
他自言自语地说很多话,从小时候的窘事到对陈宏发的惧怕,说到工作压力其实很大,他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处理的很好。他其实摇摇欲坠,很多时候想放弃一切回到家,可他知道他不能。可这些张珍都听不到,要不是还有微弱的呼吸,陈沂总觉得这刻是永别。
后来他开始祈求,祈求张珍可以坚持到过年那天,至少他还能经历一次团圆。
除夕夜前一天,陈沂买肉,搅了两种不同的饺子馅,从面袋子里掏出白面揉成团。
张珍居然又有了些精神,说,“馅里放些五香粉,吃起来香。”
陈沂欣喜若狂地应了,眼泪却差点落下来。
他在一旁忙绿,张珍就躺在那看着,口齿不清地嘱咐一些东西,“油要多一些,馅不用剁的太碎,现在用什么粉碎机,那东西哪有自己切的好。”
陈沂点头,说:“明天您要多吃几个。”
大年二十九的夜里格外冷,陈沂明明填了很多柴,却还是控制不住发抖。
晚上十一点,他又去填了一次柴,回来的时候发现张珍居然没有睡。
陈沂问:“妈,吵醒你了吗?”
张珍说,“没有,你扶我起来吧。把你姐也叫来。”
陈沂扶着人坐了起来,和陈盼一起坐在她身边,听她口齿不清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话,她说自己没有享福的命,说你们两个互相照应着,我很放心。
张珍半闭着眼睛,陈沂有一瞬间觉得那双眼睛里竟然一点光亮都没有了。
她握住一双儿女的手,眼角湿润,说:“陈沂要抓紧,人大事,妈等不到抱孙子了。但妈已经放心了。”
陈沂问:“放心什么?”
“每天晚上打着电话呢,妈知道。你有着落,妈也就安心了。”
陈沂心里一凉,知道这是误会,但是这种境况,他说不出来刺激人的话,只好将错就错地点了点头。
张珍闭上眼睛很久没说话,陈盼一滴泪垂着又被她收回,老太太偏心了一辈子,临死了对她一句话都没有,她觉得自己的难过都是多余。
可是沉默了一会儿,张珍突然又开了口。她声音太小了,需要凑得很近才能听见。
陈沂凑过去,然后示意陈盼赶紧过来。陈盼愣了一瞬,明知道肯定不是对自己说的话,还是没忍住跟了过去。
她闻见腐败和衰老的味道,天气干燥,但一直躺在这里还是会发潮。
她听见张珍叫她的名字,说:“盼啊。”
那一刻她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潸然泪下,下一句也紧跟着过来,她看见母亲瘦小的身躯,风箱一样漏气的胸膛,好像用尽了全身力气说,“妈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
腊月二十九晚上,张珍还是没等到除夕夜就彻底咽气。
窗外刮起来了风,有雪花被吹到窗外的玻璃上。
陈沂愣着叫了几句妈,却没有人能再应了。
空气陷入沉静,片刻后陈沂听到有小孩子的声音,不止一个,争着吵着喊哥哥,要晏崧带他们去玩。
晏崧的声音无奈又温柔,说,“一会儿就过去。”
小孩子好奇,问:“在跟谁打电话,是不是女朋友啊?”
“不是。”晏崧否认。
“那就是男朋友咯!”
晏崧走远了,声音越来越小,陈沂的心脏倏地抓紧,他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些什么,可他这里实在太静了,即便那么远他还是听见了晏崧的回答,“肯定不是,你们跟谁学的这些东西?小小年纪不学好!”
另一个小孩的声音传过来,“就是就是,哥哥这么喜欢和我们玩,怎么会是同性恋?”
晏崧不知道孩子的逻辑是什么来的,觉得自己跟小孩实在说不通,无奈地笑了笑。
陈沂苦笑一声,恨自己早知道结果还抱有期待。他把电话挂了,刚才所有想宣之于口的难过也都咽回到了肚子里,那些多余的感动轻轻一戳就碎了,他并没有什么立场要晏崧的安慰和原谅,这几句话彻底点醒了他。
不久之后晏崧电话打了又打了过来,问陈沂为什么挂断电话。
陈沂回:“还以为你在忙。”
晏崧难得解释,“出来吃饭,亲戚家的孩子总是缠着我。”
陈沂牵强地笑笑,声音上听不出奇怪,“你很招小孩子喜欢呢。”
晏崧皱了皱眉,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又从陈沂的语气听不出来什么问题。他顺着陈沂的话开口,不自觉透露出些真实情绪,“看起来和气些而已,总不能说烦。”
陈沂内心一震,不知道该回些什么,怕自己露出端倪,说:“我要睡了。”
晏崧知道他舟车劳顿,大发慈悲:“行,电话不要挂。”
手机亮了一夜,陈沂不知道这算什么。
他看着外面的雪花由小变大,空气越来越冷,从前到现在的日子像是走马灯。他又不自觉地流泪,不发出声音的流泪他同样习惯,即便打了一晚上的电话晏崧也没有发现奇怪。
手机没电的时候电话挂断,陈沂听见了电话里传来的平稳的呼吸。
他也闭上眼睛,发现睁眼和闭眼竟然没有区别,同样看不到明天。
第53章 新年…快乐
雪下了一夜,陈沂被阳光晒醒,推开门遍地都是雪白的。不远处有烟囱在冒烟,村里的日子谁家起床谁家做饭只需要看这个就清清楚楚。
陈沂小时候只需要看自己家里的烟囱有没有烟就知道是不是该回家吃饭。但是现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即便快要过年,燃起来的烟囱也只有寥寥几个。
张珍当时说要回来,便是想念这里年轻时候跟她一起聊家常,一起外出打工的朋友,没想到回来了,村里的人倒是都走了。
陈沂先去捡柴,把火点燃烧热室内,才从满是灰尘的库房里找出两把了锈的铁锹。
新雪下压着积雪,下面的积雪是化了又冻上的,格外难铲。陈沂长时间不运动,没什么力气,动了两下就出了点虚汗。他不知不觉产了一上午,直到从房子门口到院子门口铲出一条可以走的通路,陈沂的手已经被冻的通红。
中午吃过饭他又去铲,投入在体力劳动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用想,他终于看见了积雪下压着的从砖缝里长出来的草,枯萎的叶子下,根却带着一点绿,陈沂把几颗连品种都称不上的杂草移栽到了阳台上的花盆里,妄图从这里面看到一点机。
张珍醒来的时候看见了阳台上的植物,笑话陈沂天真,这草早就被冻死了,怎么可能再长起来。她像草叶子一样枯黄的手覆盖在陈沂手上,说:“要长起来也是从籽开始长,这棵植物的寿数就到这了。”
陈沂摇摇头,执拗道:“不会的,屋里这么暖和,它会长起来的。”
还真如他所说,这草在栽进去的第三天,盆里真长出来点嫩芽。张珍的精神这些天也好了很多,陈盼说这是因为儿子回来了心里高兴。
陈沂却觉得是因为这棵草,他居然把希望寄托在一棵草上。
院子里越来越干净,陈沂拿着推车一车一车把积雪运出去,院子里开始井井有条,天气好的时候他把张珍放在轮椅上推出去晒太阳,晴天的时候不那么冷,房檐下化得都是水,陈沂不敢让人在外面太长时间。
白天体力劳动太多,晚上陈沂会接到晏崧的电话,聊不上几句,陈沂的活实在单调,晏崧的活他也没有立场探究,他只能听见电话里存在的呼吸声,很多次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连通着的电话很多次把他拉回现实。
陈沂知道现在不是晏崧需要自己,而是他需要晏崧。
他希望日子也可以像这一刻一样停止,张珍的精神越来越好,白天时候可以说一些年轻时候的事情,陈沂问她,不恨陈宏发吗?
张珍浑浊的眼睛看得很远,但眼里却是那么平静,她说:“都过去了。”
人死如灯灭,是都过去了。
陈沂觉得那样的日子也离自己很远很远,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情绪可以从身体里抽离出来,整个人都是恍惚的,把希望和执念寄托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事物上,有时候是院子里的积雪,有时候是阳台上的草。
离除夕越来越近,张珍的精神骤然变差,连话都说不完整。
陈沂想起来很多小时候的传闻,说年纪大的老人如果撑过冬天就可以再活下去一年,说人心里的一桩心事放下彻底没念想的时候会彻底腐败下去。他已经不祈求撑过冬天,他只想至少过了这个除夕。
从腊八到小年,那颗草变软,变潮,最后一点绿被吞噬,陈沂浇了太多水,一颗野草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希望,死得不能再死,手按上去流出来的都是脓。
它没有挺到除夕,就彻底和泥土化作一起。
陈沂开始在陈盼跟前守夜,和陈盼轮着,隔一会儿探一探张珍的呼吸。他看张珍合上的满是皱纹的眼皮,头上的帽子快能盖住整个脑袋。
他自言自语地说很多话,从小时候的窘事到对陈宏发的惧怕,说到工作压力其实很大,他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处理的很好。他其实摇摇欲坠,很多时候想放弃一切回到家,可他知道他不能。可这些张珍都听不到,要不是还有微弱的呼吸,陈沂总觉得这刻是永别。
后来他开始祈求,祈求张珍可以坚持到过年那天,至少他还能经历一次团圆。
除夕夜前一天,陈沂买肉,搅了两种不同的饺子馅,从面袋子里掏出白面揉成团。
张珍居然又有了些精神,说,“馅里放些五香粉,吃起来香。”
陈沂欣喜若狂地应了,眼泪却差点落下来。
他在一旁忙绿,张珍就躺在那看着,口齿不清地嘱咐一些东西,“油要多一些,馅不用剁的太碎,现在用什么粉碎机,那东西哪有自己切的好。”
陈沂点头,说:“明天您要多吃几个。”
大年二十九的夜里格外冷,陈沂明明填了很多柴,却还是控制不住发抖。
晚上十一点,他又去填了一次柴,回来的时候发现张珍居然没有睡。
陈沂问:“妈,吵醒你了吗?”
张珍说,“没有,你扶我起来吧。把你姐也叫来。”
陈沂扶着人坐了起来,和陈盼一起坐在她身边,听她口齿不清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话,她说自己没有享福的命,说你们两个互相照应着,我很放心。
张珍半闭着眼睛,陈沂有一瞬间觉得那双眼睛里竟然一点光亮都没有了。
她握住一双儿女的手,眼角湿润,说:“陈沂要抓紧,人大事,妈等不到抱孙子了。但妈已经放心了。”
陈沂问:“放心什么?”
“每天晚上打着电话呢,妈知道。你有着落,妈也就安心了。”
陈沂心里一凉,知道这是误会,但是这种境况,他说不出来刺激人的话,只好将错就错地点了点头。
张珍闭上眼睛很久没说话,陈盼一滴泪垂着又被她收回,老太太偏心了一辈子,临死了对她一句话都没有,她觉得自己的难过都是多余。
可是沉默了一会儿,张珍突然又开了口。她声音太小了,需要凑得很近才能听见。
陈沂凑过去,然后示意陈盼赶紧过来。陈盼愣了一瞬,明知道肯定不是对自己说的话,还是没忍住跟了过去。
她闻见腐败和衰老的味道,天气干燥,但一直躺在这里还是会发潮。
她听见张珍叫她的名字,说:“盼啊。”
那一刻她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潸然泪下,下一句也紧跟着过来,她看见母亲瘦小的身躯,风箱一样漏气的胸膛,好像用尽了全身力气说,“妈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
腊月二十九晚上,张珍还是没等到除夕夜就彻底咽气。
窗外刮起来了风,有雪花被吹到窗外的玻璃上。
陈沂愣着叫了几句妈,却没有人能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