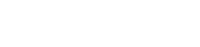“我们家的丫鬟都是好人家里的女儿,更是我细细调养过的,论相貌,我薛淑仪不敢说帝京,单说整座幽州城就没几个及得上我身边的侍女,怎得就配不上他们这群兵痞了?如今更是连我好好的儿子都带坏了!”
见发妻怨怼、丫鬟垂泪,向来高高在上的李世子没能想到这次相看大抵是要告吹了。
当夜,长随来报:“昨儿个,我送回春堂的大夫回去,哪成想里面忘八的白眼狼,竟对咱们李府口出狂言,说世子您……拿出身不入流的侍女搪塞他们。”
李世子听后默然不语,想道:“那群小兵脾气急切,见不到丫鬟的时候便嚷嚷着‘破门’,焉知自己被拒绝,岂不会对我生出怨怼之言?若我强行把侍女嫁过去,恐怕他们不仅不会领情,还会令我府上下生出嫌隙。”
陆贞柔以前可没少看什么《分手后前男友造谣我是捞女》《男同事被拒后恼羞成怒说我是卖的》,想来古代男人也是差不多,再稍稍拿奴籍点醒一下——
他们便跟被风吹的火一样,往陆贞柔想要的方向烧去。
保媒这活,自古至今都是吃力不讨好。
李世子想拿薛夫人的丫鬟强行安抚士兵的心,那就拿李旌之、李旌之拿捏薛夫人的心,再引那群口无遮拦的汉子失言几句,把话传到李世子的耳朵里,让李世子也与他们离心。
多厢争执之下,李世子的如意算盘必然要面临落空,此时丫鬟们才有利可图,不至于从李府被卖去不知何处的地方。
得知是自己的人口出狂言,李世子又急又气,当夜边宿在薛夫人房中。
夫妻俩厮磨半天,总算解开话结。
被薛婆子支招的薛夫人道:“不如销了奴籍,赎了契书,施恩于她们。等丫鬟到了年龄,我让薛妈妈、路妈妈把她们认为干女儿,做你我义妹,把人风风光光地嫁给门生,以作咱们家的助力,以后也可常来往。”
李世子沉吟片刻:“是,原本我是这个打算,奴籍不算什么事,还能博一个宽厚的美名。这契书更是简单,只是这认义女的事……”说道这儿,到底顾及自家的面子,李世子倒有些犹豫起来。
薛夫人主持中馈,自然知道这群丫鬟一到十五岁便能领到前几年的月钱用来赎身,道:“这有什么,账房横竖要给她们几两银子,这又用不了多少花销。义妹更只是个叫法,汉代的和亲公主不也是一个名儿,你难道比皇帝还体面尊贵?再说了,咱们又不是全部都认,我挑点忠心的丫鬟,让薛妈妈认上一认也无妨,还能拿出来说道说道,留一个面子情,如此这般……”
……
自从那日相看后,李府上下好似没有当过这回事一样。
到了李旌之十五岁生辰时,薛夫人于院内摆了好酒好菜,感念儿子又平安了一岁。
连李世子都从军营里骑快马赶来,带着几个老同袍过来喝了一口好大儿的生辰酒。
那几位同袍眼睛炯炯有神,身材健壮,一看就知是精兵良将,他们各自送上了一些如马鞭、环佩之类的礼物。
薛夫人让香晴一一收了,暗地嘱咐道:“回头就扔到箱子里去,不许再拿出来。”
虽然许多丫鬟小厮不太喜欢这位旌之少爷,但今日是人家生辰,往日不过是小孩子家的争端,眼下他正逢喜事,便遂了薛夫人的意思,一声声祝贺“旌之少爷平平安安”。
陆贞柔随大流跟着敬了一杯,等她放下酒杯,见别人一家热热闹闹的,干脆先撇了酒席,接口回到房里做丫鬟铺床暖被的活计。
幽州城地处北方,天气冷得极快。
十月份在南方算是温暖和乐的季节,但在这儿,被丫鬟精心照顾的花园草木已经开始佩上霜刀。
李旌之在外间脱下沾满寒气的大袍,心想:“里头这么安静,莫非是睡着了?”
念及此处,李旌之蹑手蹑脚进里间,却发现桌上点着一盏小灯,披着外袍的陆贞柔咬着细线,手指紧捏袖口,正在缝制细棉的里衣。
一见李旌之来,她“啊”地一声,赶忙收起针线活,同时忍不住皱起秀眉,似乎是被针刺伤到了。
李旌之顿时心疼极了,他搂过陆贞柔,握着她的手仔仔细细瞧了瞧:“副小姐最近怎么还勤俭起来了?我李家不大,但不差你我身上这几尺布匹。”
陆贞柔见他的心神全在自己的一双手上,当即放下心来,任由李旌之捏着手,道:“新衣的袖子太长了,我想把它缝折起来,等过两个月,我长大了再拆下来,这样衣服也能多穿几个月,不至于让路妈妈说我奢侈,说我每个月都要费人裁一身新衣裳。”
李旌之将里衣推到一边,又起身拿了盏青釉的烛台来,他拉过陆贞柔的手,借着烛光仔仔细细检查手指伤口,认认真真对着轻颤的指尖吹着气,时不时望一望陆贞柔的脸色,问她疼不疼。
听见陆贞柔语含抱怨,他劝道:“管她呢,又不是让她给你做衣服。”
话语之中带着大少爷惯有的脾气。
陆贞柔瞧了他好一会儿,神色渐渐放松下来。
见李旌之想要瞧瞧她的女红,陆贞柔想也不想便反握住李旌之的手,一口气吹灭两盏油灯,紧接着黑暗之中似乎有衣袍落地的声响与少女轻呼的嗔怪。
陆贞柔替李旌之解开衣带,纳闷道:“不再多喝两杯?”
“我答应你戒酒了,光喝水没甚意思。”李旌之哼哼道,话里带着细碎的玉器砸地声,“再说了,人家拿我做筏子牵线保姻缘的,我有什么办法。”
“今年你什么时候回帝京?”
“等父亲的调令到,前几天就听说帝京一个月前便已经派遣使者,想必就是这几天了。”李旌之褪下衣物,平日里凌厉的眉峰此刻舒展开。
他低头见陆贞柔披着一袭外袍,月色下的少女眉眼带着几分慵懒的靡丽,如玉人拥雪点朱脂,心下不由得一动,将她横抱而起。
在猝不及防的慌乱过去,接着便是陆贞柔无比熟悉的赤裸坦诚。
没过多久,纱帐之中渐渐响起暧昧的水渍声与沉重的喘息。
纱帐里只余了一盏月牙,光晕漫过两人交迭的身影时,陆贞柔躺在他臂弯中喘息着,后背紧贴着他的手臂。
李旌之的手臂结实有力,稳稳托着少女脊背,掌心上下摩挲着纤细的腰肢,透过相触的肌肤,陆贞柔能够清晰感受到属于李旌之脉搏的跳动……以及腿间突突跳动的淫器。
见发妻怨怼、丫鬟垂泪,向来高高在上的李世子没能想到这次相看大抵是要告吹了。
当夜,长随来报:“昨儿个,我送回春堂的大夫回去,哪成想里面忘八的白眼狼,竟对咱们李府口出狂言,说世子您……拿出身不入流的侍女搪塞他们。”
李世子听后默然不语,想道:“那群小兵脾气急切,见不到丫鬟的时候便嚷嚷着‘破门’,焉知自己被拒绝,岂不会对我生出怨怼之言?若我强行把侍女嫁过去,恐怕他们不仅不会领情,还会令我府上下生出嫌隙。”
陆贞柔以前可没少看什么《分手后前男友造谣我是捞女》《男同事被拒后恼羞成怒说我是卖的》,想来古代男人也是差不多,再稍稍拿奴籍点醒一下——
他们便跟被风吹的火一样,往陆贞柔想要的方向烧去。
保媒这活,自古至今都是吃力不讨好。
李世子想拿薛夫人的丫鬟强行安抚士兵的心,那就拿李旌之、李旌之拿捏薛夫人的心,再引那群口无遮拦的汉子失言几句,把话传到李世子的耳朵里,让李世子也与他们离心。
多厢争执之下,李世子的如意算盘必然要面临落空,此时丫鬟们才有利可图,不至于从李府被卖去不知何处的地方。
得知是自己的人口出狂言,李世子又急又气,当夜边宿在薛夫人房中。
夫妻俩厮磨半天,总算解开话结。
被薛婆子支招的薛夫人道:“不如销了奴籍,赎了契书,施恩于她们。等丫鬟到了年龄,我让薛妈妈、路妈妈把她们认为干女儿,做你我义妹,把人风风光光地嫁给门生,以作咱们家的助力,以后也可常来往。”
李世子沉吟片刻:“是,原本我是这个打算,奴籍不算什么事,还能博一个宽厚的美名。这契书更是简单,只是这认义女的事……”说道这儿,到底顾及自家的面子,李世子倒有些犹豫起来。
薛夫人主持中馈,自然知道这群丫鬟一到十五岁便能领到前几年的月钱用来赎身,道:“这有什么,账房横竖要给她们几两银子,这又用不了多少花销。义妹更只是个叫法,汉代的和亲公主不也是一个名儿,你难道比皇帝还体面尊贵?再说了,咱们又不是全部都认,我挑点忠心的丫鬟,让薛妈妈认上一认也无妨,还能拿出来说道说道,留一个面子情,如此这般……”
……
自从那日相看后,李府上下好似没有当过这回事一样。
到了李旌之十五岁生辰时,薛夫人于院内摆了好酒好菜,感念儿子又平安了一岁。
连李世子都从军营里骑快马赶来,带着几个老同袍过来喝了一口好大儿的生辰酒。
那几位同袍眼睛炯炯有神,身材健壮,一看就知是精兵良将,他们各自送上了一些如马鞭、环佩之类的礼物。
薛夫人让香晴一一收了,暗地嘱咐道:“回头就扔到箱子里去,不许再拿出来。”
虽然许多丫鬟小厮不太喜欢这位旌之少爷,但今日是人家生辰,往日不过是小孩子家的争端,眼下他正逢喜事,便遂了薛夫人的意思,一声声祝贺“旌之少爷平平安安”。
陆贞柔随大流跟着敬了一杯,等她放下酒杯,见别人一家热热闹闹的,干脆先撇了酒席,接口回到房里做丫鬟铺床暖被的活计。
幽州城地处北方,天气冷得极快。
十月份在南方算是温暖和乐的季节,但在这儿,被丫鬟精心照顾的花园草木已经开始佩上霜刀。
李旌之在外间脱下沾满寒气的大袍,心想:“里头这么安静,莫非是睡着了?”
念及此处,李旌之蹑手蹑脚进里间,却发现桌上点着一盏小灯,披着外袍的陆贞柔咬着细线,手指紧捏袖口,正在缝制细棉的里衣。
一见李旌之来,她“啊”地一声,赶忙收起针线活,同时忍不住皱起秀眉,似乎是被针刺伤到了。
李旌之顿时心疼极了,他搂过陆贞柔,握着她的手仔仔细细瞧了瞧:“副小姐最近怎么还勤俭起来了?我李家不大,但不差你我身上这几尺布匹。”
陆贞柔见他的心神全在自己的一双手上,当即放下心来,任由李旌之捏着手,道:“新衣的袖子太长了,我想把它缝折起来,等过两个月,我长大了再拆下来,这样衣服也能多穿几个月,不至于让路妈妈说我奢侈,说我每个月都要费人裁一身新衣裳。”
李旌之将里衣推到一边,又起身拿了盏青釉的烛台来,他拉过陆贞柔的手,借着烛光仔仔细细检查手指伤口,认认真真对着轻颤的指尖吹着气,时不时望一望陆贞柔的脸色,问她疼不疼。
听见陆贞柔语含抱怨,他劝道:“管她呢,又不是让她给你做衣服。”
话语之中带着大少爷惯有的脾气。
陆贞柔瞧了他好一会儿,神色渐渐放松下来。
见李旌之想要瞧瞧她的女红,陆贞柔想也不想便反握住李旌之的手,一口气吹灭两盏油灯,紧接着黑暗之中似乎有衣袍落地的声响与少女轻呼的嗔怪。
陆贞柔替李旌之解开衣带,纳闷道:“不再多喝两杯?”
“我答应你戒酒了,光喝水没甚意思。”李旌之哼哼道,话里带着细碎的玉器砸地声,“再说了,人家拿我做筏子牵线保姻缘的,我有什么办法。”
“今年你什么时候回帝京?”
“等父亲的调令到,前几天就听说帝京一个月前便已经派遣使者,想必就是这几天了。”李旌之褪下衣物,平日里凌厉的眉峰此刻舒展开。
他低头见陆贞柔披着一袭外袍,月色下的少女眉眼带着几分慵懒的靡丽,如玉人拥雪点朱脂,心下不由得一动,将她横抱而起。
在猝不及防的慌乱过去,接着便是陆贞柔无比熟悉的赤裸坦诚。
没过多久,纱帐之中渐渐响起暧昧的水渍声与沉重的喘息。
纱帐里只余了一盏月牙,光晕漫过两人交迭的身影时,陆贞柔躺在他臂弯中喘息着,后背紧贴着他的手臂。
李旌之的手臂结实有力,稳稳托着少女脊背,掌心上下摩挲着纤细的腰肢,透过相触的肌肤,陆贞柔能够清晰感受到属于李旌之脉搏的跳动……以及腿间突突跳动的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