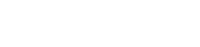陆贞柔的身体瞬间被臊得一层瑰丽的粉,她气得推了推李旌之,见李旌之愈发来劲,甚至压着她的臀开始射精。
感受到腿间湿润粘稠,陆贞柔登时霞飞双颊,委屈说道:“旌之大少爷好没道理,竟拉我这个小小婢女行这等白日宣淫之事。”说完,少女目光盈盈,竟要落下泪似的。
等小旌之冷下来,李旌之的头脑亦渐渐开始清醒,他见陆贞柔含泪诉控的样子,心下瞬间软成一团,想也不想便拉进怀里哄着。
哄了半天,又是求饶讨好,又是低声下气认错,陆贞柔这才渐渐止住哭声。
这时,李旌之放心地掀了被子准备起床。
哪知两人的身体一暴露在空气中,李旌之往床上一瞧——少女侧跪于床榻之上,双腿随姿态自然敞开,双膝微微错开,小腿与脚踝纤瘦精巧,大腿线条柔和还印着他留下的指痕。
见李旌之看来,因剧烈情事而脸颊尚在绯红的陆贞柔十分诱人。
李旌之见她不解地回望过来,少女精致的前膝轻抵床面,带着交错指痕的雪色臀瓣稍抬并未落座于脚跟上,而是借着膝盖的支撑微微悬在湿漉漉的床单处,两膝之间——如桃花沾露的景色一览无余。
顺着李旌之直勾勾的目光,跪坐的陆贞柔看向自己的腿间——原来是李旌之射出的白浊正挂在花瓣似的穴儿口处,像是清晨窗台的萼片挂着露珠似的,似垂非垂地悬在穴儿处。
陆贞柔瞬间脸色涨的通红,慌忙地将床褥堆在自己面前,她越想越委屈,胸膛起伏不定,声音也开始抽抽噎噎的,眼下——竟是又被气哭了。
李旌之心荡神驰,仍沉浸名花含露似的风景中,并未从少女的羞处移开目光,只是一听见陆贞柔抽泣的声音,又有了反应。
被陆贞柔训了多年,几乎是形成反射弧一样的李旌之来不及穿上衣服,便上前一步将赤裸的少女搂在怀中,大少爷脾气的李旌之竟对一个婢女低眉顺眼、好声好气地哄着。
面对陆贞柔的责骂殴打,李旌之心知自己唐突,并不做反抗,而是一一受了。
不知道闹腾了多久,终于等到陆贞柔气性渐消,李旌之这才讨好似的吻去少女脸颊上的泪痕。
见陆贞柔仍是垂泪不语的样子,李旌之急中生智地说道:“都怪昨晚哪壶黄汤误事,卿卿贞柔原谅我这一回,我此后再也不喝酒了。”
经此一遭,已经辰时。
三道门大院正堂,薛夫人并着丫鬟婆子眼巴巴等着丈夫孩子一起过来吃饭。
只是眼下小厨房都备好热菜了,李世子那边说是要陪扬武、建威二位将军去城郊军营共进早膳,操练士兵,还让薛夫人转告两位少爷,让他们用完饭后便来军营操练。
而眼下,李旌之、李旗之两兄弟还没出现。
向来和善的路妈妈皱起眉头,道:“今天旌之少爷又晚起了?莫不是璧月唆使的?”
红玉笑道:“路妈妈这话好没道理,璧月才跟旌之少爷相处多久?他一个月有二十天在营里哩!人家璧月在家里好歹能劝一劝,前几年您不在的时候,只剩下乳兄弟陪着旌之少爷,结果他却不起来了。路妈妈若是不信,或是看一看旗之少爷,或是再支使个人去旌之少爷房里,省得说我偏心璧月那丫头。”
与红玉昨夜打过商量的薛婆子道:“红玉说的是极,那群丘八脾气,说白了以前就是个缺管少教的混混。”
“想当初,咱们初来这幽州城时,把璧月放在旌之房里,咱们旌之也是丁卯似的,眼巴巴过来给夫人您请安,如今竟是如此惫懒,真怕旌之、旗之这两个乖孩子染上什么不好的习性,学了那营地里的粗俗脾性。”
红玉与薛婆子的一席话说到了薛夫人心坎里。
她自然是不会怪两个儿子贪睡的,只是一厢情愿地想道:“昨夜香晴这个丫头说得对,想来里面都是缺管少教的混混地痞,旌之能跟他们学到什么好?以后说不定这群忘八端的东西推我儿子去死。”
“再说了,旗之从小便乖巧,如今不过是演练了一会儿,竟也跟着忘了他的母亲。”
薛夫人想清楚关窍,只是碍于夫君的面子不好说什么,心下仍有些不痛快,只得说道:“先开饭。”
不知道是不是大院里的粗人们冲撞了李府气运,薛夫人不过拿起筷子,挑拣了一二样的小食,便被酸倒了牙,当即啐道:“怎么的饭菜怎么咸了?小厨房今日是谁当值?”
绿芽道:“回夫人,是香雨。”
薛夫人一拍桌子,怒气正好无从发泄:“让她过来!”
被带上来的香雨并不说什么,只是一昧跪地谢罪。
路妈妈见她面色有异,又瞥见薛婆子双唇微张,便想着抢在薛婆子面前做个善人,因而劝道:“夫人,香雨在厨房做事一向利落,眼下怕不是有什么内情。”
薛夫人想起院里的那些个烦人的汉子,忍下气性,道:“香雨,我待你素来不薄,你若是有什么委屈,与我一并说了就是。”
香雨忽地流下泪来,哽咽道:“夫人恕罪,奴婢一大早便心慌意乱,想起昨儿个那群人好没意思,竟然骂我们姐妹是奴籍出身,还、还说,等幽州再被羌人攻破,便要趁机把我们掳进帐子里去,反正也只是遭贱的奴儿。”
薛夫人不可置信,道:“竟有此事?”
丫鬟齐刷刷地跪了一片,或是沉默不语,或是如香雨一样垂着泪。
薛夫人怒极反笑:“好、好好好,好个李鹤年。”说完,便立刻差人去军营问话。
这话早上才说,晌午时才传到李世子耳朵里,在座的扬武、建威二位将军也是吃了一惊。
他们知晓一些兵痞脾性,什么话都说出来,这话八九不离十。
李世子顾及同袍情谊,当即辩驳道:“我想这些话也只是某些不省事的气话。”实则心里已经信了七八分。
蔺方古道:“贤弟此言差矣,此事分轻重缓急,想必是有小人在背后搬弄是非,眼下还是安慰弟妹为主。”
要是薛夫人极力反对,加上丫鬟不肯配合,这事怎么着都得解下仇怨,保不齐要吃一堆言官的官司。
李府内——
正在三道门后请安的陆贞柔乖巧地站在丫鬟堆里,听着薛夫人向李旌之两兄弟大吐苦水。
她知道那群汉子气急,不过没见着面便要“破门”,因此只需要茶安这个丫头,用些似是非似的风言风语,像是无心闲话一激,他们便什么话都能说出口。
正巧昨天,宁回跟着李府的小厮听得清清楚楚。
薛夫人谈到“羌人”,又怜惜自己的儿子在军营历练,想到香晴说的“刀剑无眼”,便忍不住心惊胆颤,边哭边骂道:“都是黄汤灌下肚里,昏了头了?”
李世子风风火火归家时,正撞薛夫人的枪口上。
只见素来宽厚的薛夫人冲李世子冷笑,道:“好个威风的将军,好个蛮横的军爷。”
感受到腿间湿润粘稠,陆贞柔登时霞飞双颊,委屈说道:“旌之大少爷好没道理,竟拉我这个小小婢女行这等白日宣淫之事。”说完,少女目光盈盈,竟要落下泪似的。
等小旌之冷下来,李旌之的头脑亦渐渐开始清醒,他见陆贞柔含泪诉控的样子,心下瞬间软成一团,想也不想便拉进怀里哄着。
哄了半天,又是求饶讨好,又是低声下气认错,陆贞柔这才渐渐止住哭声。
这时,李旌之放心地掀了被子准备起床。
哪知两人的身体一暴露在空气中,李旌之往床上一瞧——少女侧跪于床榻之上,双腿随姿态自然敞开,双膝微微错开,小腿与脚踝纤瘦精巧,大腿线条柔和还印着他留下的指痕。
见李旌之看来,因剧烈情事而脸颊尚在绯红的陆贞柔十分诱人。
李旌之见她不解地回望过来,少女精致的前膝轻抵床面,带着交错指痕的雪色臀瓣稍抬并未落座于脚跟上,而是借着膝盖的支撑微微悬在湿漉漉的床单处,两膝之间——如桃花沾露的景色一览无余。
顺着李旌之直勾勾的目光,跪坐的陆贞柔看向自己的腿间——原来是李旌之射出的白浊正挂在花瓣似的穴儿口处,像是清晨窗台的萼片挂着露珠似的,似垂非垂地悬在穴儿处。
陆贞柔瞬间脸色涨的通红,慌忙地将床褥堆在自己面前,她越想越委屈,胸膛起伏不定,声音也开始抽抽噎噎的,眼下——竟是又被气哭了。
李旌之心荡神驰,仍沉浸名花含露似的风景中,并未从少女的羞处移开目光,只是一听见陆贞柔抽泣的声音,又有了反应。
被陆贞柔训了多年,几乎是形成反射弧一样的李旌之来不及穿上衣服,便上前一步将赤裸的少女搂在怀中,大少爷脾气的李旌之竟对一个婢女低眉顺眼、好声好气地哄着。
面对陆贞柔的责骂殴打,李旌之心知自己唐突,并不做反抗,而是一一受了。
不知道闹腾了多久,终于等到陆贞柔气性渐消,李旌之这才讨好似的吻去少女脸颊上的泪痕。
见陆贞柔仍是垂泪不语的样子,李旌之急中生智地说道:“都怪昨晚哪壶黄汤误事,卿卿贞柔原谅我这一回,我此后再也不喝酒了。”
经此一遭,已经辰时。
三道门大院正堂,薛夫人并着丫鬟婆子眼巴巴等着丈夫孩子一起过来吃饭。
只是眼下小厨房都备好热菜了,李世子那边说是要陪扬武、建威二位将军去城郊军营共进早膳,操练士兵,还让薛夫人转告两位少爷,让他们用完饭后便来军营操练。
而眼下,李旌之、李旗之两兄弟还没出现。
向来和善的路妈妈皱起眉头,道:“今天旌之少爷又晚起了?莫不是璧月唆使的?”
红玉笑道:“路妈妈这话好没道理,璧月才跟旌之少爷相处多久?他一个月有二十天在营里哩!人家璧月在家里好歹能劝一劝,前几年您不在的时候,只剩下乳兄弟陪着旌之少爷,结果他却不起来了。路妈妈若是不信,或是看一看旗之少爷,或是再支使个人去旌之少爷房里,省得说我偏心璧月那丫头。”
与红玉昨夜打过商量的薛婆子道:“红玉说的是极,那群丘八脾气,说白了以前就是个缺管少教的混混。”
“想当初,咱们初来这幽州城时,把璧月放在旌之房里,咱们旌之也是丁卯似的,眼巴巴过来给夫人您请安,如今竟是如此惫懒,真怕旌之、旗之这两个乖孩子染上什么不好的习性,学了那营地里的粗俗脾性。”
红玉与薛婆子的一席话说到了薛夫人心坎里。
她自然是不会怪两个儿子贪睡的,只是一厢情愿地想道:“昨夜香晴这个丫头说得对,想来里面都是缺管少教的混混地痞,旌之能跟他们学到什么好?以后说不定这群忘八端的东西推我儿子去死。”
“再说了,旗之从小便乖巧,如今不过是演练了一会儿,竟也跟着忘了他的母亲。”
薛夫人想清楚关窍,只是碍于夫君的面子不好说什么,心下仍有些不痛快,只得说道:“先开饭。”
不知道是不是大院里的粗人们冲撞了李府气运,薛夫人不过拿起筷子,挑拣了一二样的小食,便被酸倒了牙,当即啐道:“怎么的饭菜怎么咸了?小厨房今日是谁当值?”
绿芽道:“回夫人,是香雨。”
薛夫人一拍桌子,怒气正好无从发泄:“让她过来!”
被带上来的香雨并不说什么,只是一昧跪地谢罪。
路妈妈见她面色有异,又瞥见薛婆子双唇微张,便想着抢在薛婆子面前做个善人,因而劝道:“夫人,香雨在厨房做事一向利落,眼下怕不是有什么内情。”
薛夫人想起院里的那些个烦人的汉子,忍下气性,道:“香雨,我待你素来不薄,你若是有什么委屈,与我一并说了就是。”
香雨忽地流下泪来,哽咽道:“夫人恕罪,奴婢一大早便心慌意乱,想起昨儿个那群人好没意思,竟然骂我们姐妹是奴籍出身,还、还说,等幽州再被羌人攻破,便要趁机把我们掳进帐子里去,反正也只是遭贱的奴儿。”
薛夫人不可置信,道:“竟有此事?”
丫鬟齐刷刷地跪了一片,或是沉默不语,或是如香雨一样垂着泪。
薛夫人怒极反笑:“好、好好好,好个李鹤年。”说完,便立刻差人去军营问话。
这话早上才说,晌午时才传到李世子耳朵里,在座的扬武、建威二位将军也是吃了一惊。
他们知晓一些兵痞脾性,什么话都说出来,这话八九不离十。
李世子顾及同袍情谊,当即辩驳道:“我想这些话也只是某些不省事的气话。”实则心里已经信了七八分。
蔺方古道:“贤弟此言差矣,此事分轻重缓急,想必是有小人在背后搬弄是非,眼下还是安慰弟妹为主。”
要是薛夫人极力反对,加上丫鬟不肯配合,这事怎么着都得解下仇怨,保不齐要吃一堆言官的官司。
李府内——
正在三道门后请安的陆贞柔乖巧地站在丫鬟堆里,听着薛夫人向李旌之两兄弟大吐苦水。
她知道那群汉子气急,不过没见着面便要“破门”,因此只需要茶安这个丫头,用些似是非似的风言风语,像是无心闲话一激,他们便什么话都能说出口。
正巧昨天,宁回跟着李府的小厮听得清清楚楚。
薛夫人谈到“羌人”,又怜惜自己的儿子在军营历练,想到香晴说的“刀剑无眼”,便忍不住心惊胆颤,边哭边骂道:“都是黄汤灌下肚里,昏了头了?”
李世子风风火火归家时,正撞薛夫人的枪口上。
只见素来宽厚的薛夫人冲李世子冷笑,道:“好个威风的将军,好个蛮横的军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