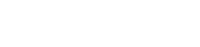齐雪死缠烂打,哭得梨花带雨,那眼泪一半真委屈,一半是无处落脚急出来的,总算磨得掌柜松口,允她一个没有工钱,只包最差通铺宿处的活儿。
她刚喘匀气,那柳放故意似的,特地订了叁楼一间上好的卧房,又流水一般点了满桌菜肴并酒,指明要她一趟趟送上楼。
楼梯陡窄,齐雪端着沉甸甸的托盘,腿肚子酸软打颤,汗水濡湿鬓角,狼狈不堪。
她将最后一碟小菜重重顿在柳放桌上时,好像能听见自己骨头咯吱作响的呼救。
齐雪胸脯因急促呼吸而起伏,咬着后槽牙道:“你的菜,上齐了!”
她实在不明白,柳放为何偏要刻意刁难自己。
柳放瞧着她这模样,心头那点莫名的火气却并未消散。他素来不喜年长者说教,更厌恶齐雪无心的所谓“承欢膝下”的规劝。
她懂什么?她可知家中的束缚与如今看似孤身的自由,孰轻孰重?
他拎起一壶酒,结果把齐雪的脚步又勾回来。
“你喝酒?你才多大,就喝酒?”
柳放眼皮都未抬:“与你何干?快走,把门带上。”
她想着,还需许大夫配制解药,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的小辈学坏,忍不住又多一句嘴:
“喝酒伤身,年纪轻轻糟蹋根本,将来肾虚,可是难有子嗣的。”
柳放心头火起,立即斟满一杯烈酒,在她面前仰头一饮而尽,喉管辛辣。
他故意用挑衅的目光回她:“我是否有子嗣,不关你的事,谁又说我一定要娶妻生子了?”
齐雪看着他原是白璧无瑕的脸庞因酒意泛红,心想他终究只有十七,在自己面前不过是个半大孩子,那点气恼便化作了无奈的叹息。
她不再多言,默默替他带上门,转身下楼,想去灶间给他倒壶清水,散散酒气。
门扉复拢,柳放愠色渐褪,取而代之的是烦闷与自嘲。
他点这酒,原不是为了饮。
少年从怀中取出一枚寒意深重的玉石,置于桌上。这玉需时时以烈酒洗涤,去除浊气。
心中郁结难舒,他不禁又闷了一口酒。洗玉的酒性子骇人热烈,后劲绵长,不知不觉间,已半壶下肚。
齐雪端着满满一壶白水,双腿即便是快化了,也强打精神一步步挪上楼。
水壶沉重,她又乏力,晃荡出的冷水溅湿了她前襟的襦裙,近夏本就衣衫单薄,湿布料紧紧贴在肌肤上,勾勒出诱人的曲线。
她行至柳放房门外,腾不出手,只得用脚尖轻轻踢了踢门板,扬声道:“开门,快开门!”
里头半晌才传来跌跌撞撞的脚步声。
门吱呀拉开,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柳放醉眼朦胧地站在门内,身形轻晃。
他循声低头,视线恰好落在齐雪被水浸湿的胸前,布料近乎透明,紧紧包裹着那丰腴起伏的轮廓。
齐雪本就气喘,吸气时仿佛两个乳房都要小兔般跳出来似的。
柳放脑中“嗡”的一声,周身血液扑腾着瞬间冲上了头顶,理智被炎炎酒气烧得灰飞烟灭,他失控地伸出手,钳住齐雪的肩膀,滚烫的身躯便要俯压下去。
“啪!啪!”
两声清脆的耳光炸响,齐雪又惊又怒,水壶早已被她掼在地上好腾出手。
她掌心涂了捏碎的薄荷叶般刺麻,浑身惊惧:“你!简直是不像话!”说着,转身就要往楼下跑,想去寻掌柜求助。
柳放被这两巴掌打得晕头转向,脸颊上红痕乍起,酒却也醒了大半。
听到她要去找别人,心中一惊,堪堪占据上风的理智让他急忙伸手去拉住她手腕。
“别……别去……”他费力将门重新关上,背靠着门板,喘息粗重,情欲与羞耻心要将他撕裂。
他强撑着弯下腰,捞起地上仅存些许清水的破壶,把那点冰凉尽数浇在自己头上。
冷水激得他一哆嗦,齐雪在旁,看着他一连串的动作,也愣住了。
好一会儿,她还是扯过干净的布巾,替他擦了擦脸上、发上的水渍,又扶着他摇摇晃晃走到榻边躺下。
“对不住……”柳放闭着眼,说话低哑。
齐雪看着他脸上清晰的指印和一点血红,语气也缓和下来:“我也……下手重了些,把你的脸都打破相了,算是扯平。”
柳放似乎极不愿被她认作是轻浮浪荡之徒,思绪挣扎片刻,还是叹了口气,将自己的过往道来。
柳佑之与池苏两小无猜,成婚后几年,一人任职县令,一人料理家中事务,不久便生下了长女柳观水。
而后便是长子,奈何长子福薄夭折,池苏承受不住打击,从此变得疯疯癫癫,柳佑之爱护左右,陪着她治病,这才在来年秋天,又有了柳放。
池苏认定柳放是长子再次投胎,对柳放不仅溺爱,更有病态的控制,当家中嬷嬷提出该断奶时,她嘶吼着把人赶出了门,就这么让柳放吃着她的奶水到了童年时期,柳放生生患上了痴乳症,发作时若不吃奶便会全身生痛。
久而久之,池苏有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就请旧相识许良想法子缓解此症,却不许他根治,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许良雕琢玉石,让柳放含在口中,便能降火褪欲,玉石又不可太过冷寂,只好以烈酒洗热,叁年一换。
齐雪听着,心中那点怨气早已被巨大的震惊和怜悯替代。
想起自己“肾虚”的刻薄话,她羞愧:“是我误会了你。”
柳放摇了摇头,认真地说:“你误会我什么都好,切莫以为……我是个随便的、专会玩弄姑娘的登徒子便是。”
齐雪轻声问:“那你现在……还和你娘……”话出口才觉不妥。
“我娘已经不在了。”柳放说,“是某年瘟疫时为百姓分粥,不慎染上病逝的。”
她陷入了更深的悲伤,可是柳放都没哭,她也没有理由哭。
她想起来二人初次靠近时,闻见的冷香,原来是他怀中玉石的气息。
“你快好好歇着吧,”她愈加温柔,“我去给你把玉石洗干净,放在你枕边。”
她起身,顺手将窗推开一些,放夜风吹来,希望能驱散室内的酒味与他身上的燥热。
不多时,柳放半梦半醒间,感觉到有人轻轻来到榻边,将一枚酒香清冽的玉石放在他枕畔。
又不知多久过去,窗外风声凌厉非常,呼啸着穿过窗棂,柳放被扰醒。
他起身,想去将窗户关小些,然而,他不经意探过窗口,看向楼下那方被客栈楼宇围合的天井时,却定住了。
她刚喘匀气,那柳放故意似的,特地订了叁楼一间上好的卧房,又流水一般点了满桌菜肴并酒,指明要她一趟趟送上楼。
楼梯陡窄,齐雪端着沉甸甸的托盘,腿肚子酸软打颤,汗水濡湿鬓角,狼狈不堪。
她将最后一碟小菜重重顿在柳放桌上时,好像能听见自己骨头咯吱作响的呼救。
齐雪胸脯因急促呼吸而起伏,咬着后槽牙道:“你的菜,上齐了!”
她实在不明白,柳放为何偏要刻意刁难自己。
柳放瞧着她这模样,心头那点莫名的火气却并未消散。他素来不喜年长者说教,更厌恶齐雪无心的所谓“承欢膝下”的规劝。
她懂什么?她可知家中的束缚与如今看似孤身的自由,孰轻孰重?
他拎起一壶酒,结果把齐雪的脚步又勾回来。
“你喝酒?你才多大,就喝酒?”
柳放眼皮都未抬:“与你何干?快走,把门带上。”
她想着,还需许大夫配制解药,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的小辈学坏,忍不住又多一句嘴:
“喝酒伤身,年纪轻轻糟蹋根本,将来肾虚,可是难有子嗣的。”
柳放心头火起,立即斟满一杯烈酒,在她面前仰头一饮而尽,喉管辛辣。
他故意用挑衅的目光回她:“我是否有子嗣,不关你的事,谁又说我一定要娶妻生子了?”
齐雪看着他原是白璧无瑕的脸庞因酒意泛红,心想他终究只有十七,在自己面前不过是个半大孩子,那点气恼便化作了无奈的叹息。
她不再多言,默默替他带上门,转身下楼,想去灶间给他倒壶清水,散散酒气。
门扉复拢,柳放愠色渐褪,取而代之的是烦闷与自嘲。
他点这酒,原不是为了饮。
少年从怀中取出一枚寒意深重的玉石,置于桌上。这玉需时时以烈酒洗涤,去除浊气。
心中郁结难舒,他不禁又闷了一口酒。洗玉的酒性子骇人热烈,后劲绵长,不知不觉间,已半壶下肚。
齐雪端着满满一壶白水,双腿即便是快化了,也强打精神一步步挪上楼。
水壶沉重,她又乏力,晃荡出的冷水溅湿了她前襟的襦裙,近夏本就衣衫单薄,湿布料紧紧贴在肌肤上,勾勒出诱人的曲线。
她行至柳放房门外,腾不出手,只得用脚尖轻轻踢了踢门板,扬声道:“开门,快开门!”
里头半晌才传来跌跌撞撞的脚步声。
门吱呀拉开,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柳放醉眼朦胧地站在门内,身形轻晃。
他循声低头,视线恰好落在齐雪被水浸湿的胸前,布料近乎透明,紧紧包裹着那丰腴起伏的轮廓。
齐雪本就气喘,吸气时仿佛两个乳房都要小兔般跳出来似的。
柳放脑中“嗡”的一声,周身血液扑腾着瞬间冲上了头顶,理智被炎炎酒气烧得灰飞烟灭,他失控地伸出手,钳住齐雪的肩膀,滚烫的身躯便要俯压下去。
“啪!啪!”
两声清脆的耳光炸响,齐雪又惊又怒,水壶早已被她掼在地上好腾出手。
她掌心涂了捏碎的薄荷叶般刺麻,浑身惊惧:“你!简直是不像话!”说着,转身就要往楼下跑,想去寻掌柜求助。
柳放被这两巴掌打得晕头转向,脸颊上红痕乍起,酒却也醒了大半。
听到她要去找别人,心中一惊,堪堪占据上风的理智让他急忙伸手去拉住她手腕。
“别……别去……”他费力将门重新关上,背靠着门板,喘息粗重,情欲与羞耻心要将他撕裂。
他强撑着弯下腰,捞起地上仅存些许清水的破壶,把那点冰凉尽数浇在自己头上。
冷水激得他一哆嗦,齐雪在旁,看着他一连串的动作,也愣住了。
好一会儿,她还是扯过干净的布巾,替他擦了擦脸上、发上的水渍,又扶着他摇摇晃晃走到榻边躺下。
“对不住……”柳放闭着眼,说话低哑。
齐雪看着他脸上清晰的指印和一点血红,语气也缓和下来:“我也……下手重了些,把你的脸都打破相了,算是扯平。”
柳放似乎极不愿被她认作是轻浮浪荡之徒,思绪挣扎片刻,还是叹了口气,将自己的过往道来。
柳佑之与池苏两小无猜,成婚后几年,一人任职县令,一人料理家中事务,不久便生下了长女柳观水。
而后便是长子,奈何长子福薄夭折,池苏承受不住打击,从此变得疯疯癫癫,柳佑之爱护左右,陪着她治病,这才在来年秋天,又有了柳放。
池苏认定柳放是长子再次投胎,对柳放不仅溺爱,更有病态的控制,当家中嬷嬷提出该断奶时,她嘶吼着把人赶出了门,就这么让柳放吃着她的奶水到了童年时期,柳放生生患上了痴乳症,发作时若不吃奶便会全身生痛。
久而久之,池苏有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就请旧相识许良想法子缓解此症,却不许他根治,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许良雕琢玉石,让柳放含在口中,便能降火褪欲,玉石又不可太过冷寂,只好以烈酒洗热,叁年一换。
齐雪听着,心中那点怨气早已被巨大的震惊和怜悯替代。
想起自己“肾虚”的刻薄话,她羞愧:“是我误会了你。”
柳放摇了摇头,认真地说:“你误会我什么都好,切莫以为……我是个随便的、专会玩弄姑娘的登徒子便是。”
齐雪轻声问:“那你现在……还和你娘……”话出口才觉不妥。
“我娘已经不在了。”柳放说,“是某年瘟疫时为百姓分粥,不慎染上病逝的。”
她陷入了更深的悲伤,可是柳放都没哭,她也没有理由哭。
她想起来二人初次靠近时,闻见的冷香,原来是他怀中玉石的气息。
“你快好好歇着吧,”她愈加温柔,“我去给你把玉石洗干净,放在你枕边。”
她起身,顺手将窗推开一些,放夜风吹来,希望能驱散室内的酒味与他身上的燥热。
不多时,柳放半梦半醒间,感觉到有人轻轻来到榻边,将一枚酒香清冽的玉石放在他枕畔。
又不知多久过去,窗外风声凌厉非常,呼啸着穿过窗棂,柳放被扰醒。
他起身,想去将窗户关小些,然而,他不经意探过窗口,看向楼下那方被客栈楼宇围合的天井时,却定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