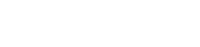周锵锵与秦阳对视一眼,皱起眉头,摇了摇头。
十分钟后,门再次被推开。
朱浩锋走进来,脚步带着几分不耐。
目光扫过众人时,他神色的冷意肉眼可见。
话不多说,他直接落座,低头开始组鼓。
没过多久,一串急促、硬朗到连喘息缝隙都不给的鼓点炸开——今日份的练习开始,尽管今日看起来不太平!
方乐文抱着吉他,指尖落下,旋律轻盈滑动,每一次上滑都带有倔强的锋芒。
秦阳踩下效果器,delay与phaser在空气中牵出道道虚影,将方乐文的旋律拉扯至时而犀利,时而飘忽。
周锵锵左手稳稳压住低音,像无声的暗流,往下托住音场;右手在和声中谨慎游走,试图将两把吉他的分歧收拢成循环。
就在此时——
朱浩锋的鼓棒敲进来。
节奏极简、精准,今天却沉重过头。
每一个鼓点落下,都仿佛钉子砸向地板,力道里带有明显的压迫。
旋律上升,效果器下沉,反之亦然;低音压制,留白空缺;鼓点平稳,在每个循环中惊鸿一现。
四种声音交相互交织,形成奇异的张力,紧绷却完整。
这张力,又有些难以言喻的如履薄冰。
果然,下一秒钟,薄冰碎裂。
不知为何,朱浩锋一个失神,鼓点空了半拍。
方乐文的吉他猛然旋律拉高,冲出整体,直接撞击在由于追赶而稍显急促的鼓点节奏上。
朱浩锋瞬间回击。
他眉头紧皱,军鼓砸下,节奏不仅补回,更是渐进,直接插入shuffle。
方乐文旋律再升。
朱浩锋节奏再紧。
一时间,工作室蜕变成搏斗场,弦与鼓互相顶上去,谁也不肯让步。
周锵锵立即加入pad想要救场,但他的键盘音被两股力量直接撕开,失控到火花四溅。
未免火上浇油,秦阳索性停下手中的吉他。
工作室瞬间仅剩下嘈杂的噪音与震动——
旋律像锋利的刀刃,鼓点似无情的重锤,两股力量再无调和,直接将周锵锵的键盘驱逐至无人区。
周锵锵意识到,吉他和鼓点的冲突进展到他无法调和的地步,不得已也停了下来。
这一停,总算惊醒梦中的方乐文与朱浩锋。
二人的乐器争端戛然而止,tereza工作室一度安静异常。
终于,方乐文骤然按住琴弦,琴声被他粗暴掐断。
他站起身来,咆哮声从胸腔迸裂而出,冲着朱浩锋:“你到底想怎么样?!忽快忽慢,你他妈在打什么节奏!?”
朱浩锋抬起头,放下鼓棒,眼神冷静:“我没有忽快忽慢,我的节奏从来没有变过!”
“你放屁!”
方乐文声音激烈,像硬压住某种濒临爆炸的东西。
他深呼吸一口,手指颤抖,却依旧刻意将那把黑色吉他轻轻放下。
他站起来,朝朱浩锋冲了过去,带着彻底失控的愤怒。
他一把揪住朱浩锋的衣领,将其从座位上拎了起来,力道大到他浑然不觉。
“我他妈就是——”
他吼到一半,像被逼到绝境,声音破碎,眼眶发红:“太容易相信你!”
周锵锵本能地上前拉架,秦阳紧随其后,站到他旁边。
“乐文,有话好说,你明知道浩锋对你……”
周锵锵想说些什么,让事情不至于变得更糟,却被方乐文的下一句震慑住。
“我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啊????”
方乐文一声诘问犹如惊雷,将所有压抑、委屈、期待、痛苦全部剖开,残酷地呈现在朱浩锋眼前。
那声音太响,太痛,太直接,导致朱浩锋的眼皮不受控制地轻颤一下。
猝不及防地,朱浩锋眨眼的须臾,方乐文的眼泪掉落下来。
周锵锵看得胸口发紧。
一路走来,方乐文为朱浩锋黯然神伤的太多时刻,他都陪在身边。
他为方乐文难过,也为朱浩锋难过,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们由于世事无常吃过的那些苦,他喉咙发酸,咬紧牙关。
在令人窒息的混乱中,朱浩锋没有沉默:
“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咬字极重,仿佛将心声按在每一个字上:“我四年前就告诉过你!我上周……再次回答了你!我的答案,从来没有变过!”
方乐文的呼吸紊乱,揪着朱浩锋衣领的指节发白。
头昏脑涨中,他再听朱浩锋继续说:
“只是!”
“只是现在的我……不能像四年前那样——自由、勇敢,想爱就爱,想疯就疯,在这个世界上只做自己想做的那种人!”
“我花了四年……去弥补对我妹、对我妈犯下的错误……”
“那我呢?!啊???”
朱浩锋的话没有让方乐文卸下心防,反而形同一把火铲,把他心中烧不透的、浇不净的火星全都刨出来,顷刻间点得更旺、更痛,更来势汹汹:
“你花这些年去弥补对莎莎的、对你家人的那些遗憾,那我呢!!!”
“为什么你牺牲的总是我!!!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给我希望、又丢下我???”
“你在耍我吗!!!”
方乐文歇斯底里的声线,震得整个tereza工作室嗡嗡作响,震碎周遭与世无争的空气,响彻朱浩锋和方乐文各自的,千山万水分隔两地思念疯长心气荒芜的四年。
“我没有耍你!”
朱浩锋不再对方乐文的质询讳莫如深,他眼底那层最后的冷静不复存在。
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个初初成长的青年人最真实的迷茫与彷徨。
“我也需要时间……去尝试弥补……永远弥补不了的遗憾……去身体力行宽慰家人,去独自一人舔舐伤口,去承认我远远不如自己以为的那样强大——强大到可以周全所有!”
“现在,我总算……”
“总算什么?”
方乐文胸口剧烈起伏,胸腔间有巨大悲愤:“总算在回美国之前,把我睡了?”
在场所有人,都因为这句话,怔住了。
朱浩锋显然未料到方乐文会用如此自轻自贱的方式定义两人的关系。
他眉头微蹙,眼睛睁大,看向方乐文的目光中尽是心痛与难以置信——泪光直接涌了上来。
“四年前,你吻了我,说永远不会离开我,可是你走了……”
“一周前,我稀里糊涂和你上了床,你趁我醉着,说让我等你……”
“可是我醒来后,好像一切都没发过?!是我对你欲求不满到出现幻觉的地步了吗?!”
“朱浩锋,回答我!!!你要把我当傻子玩弄到什么时候!!!”
方乐文再次揪起朱浩锋的衣领,恨意在眼底翻滚,爱意在心头涌动,如火苗附着于伤口上。
他死死盯住朱浩锋,像是要从他身上牵扯出一个解释,一个答案,一个只要对方开口、便能挽救过去整整四年的答案。
周锵锵循着方乐文的视线回头望去。
朱浩锋目不转睛注视着方乐文,他反手扣住方乐文的手臂,恳切地说:“再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毕业,我会……”
“等你毕业?等毕业时你妈再次哭着求你留在美国,求你结婚子,走阳关大道,然后你再一次把我像四年前一样丢在北城、丢在回忆里……?”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
方乐文好像疯了,边喊着,边甩开朱浩锋的双手,踉跄着冲向方才的座位。
周锵锵意识到不妙,刚想伸手阻止,已经来不及。
方乐文抓住那把黑色吉他。
——朱浩锋在远赴美国之前,为他挑选的十八岁成人礼,他最珍惜的宝贝。
指尖触碰到琴身的一刹那,整个人像过电一样僵在原地。
那一瞬太短,却足以让方乐文脑海中晃过所有闪回……
然而,须臾过后,冲动海潮般席卷而来,将所有回忆淹没到支离破碎。
方乐文的眼中闪过绝望的决绝,他举起那把吉他……
下一秒,整个工作室如被惊雷砸中。
黑色吉他狠狠摔在地上。
琴身先是错位,再爆裂——清脆、尖锐,带着绝望的残响,好似心脏被硬撕开。
琴弦同时崩断。
一根,两根,三根……
金属拉断时的尖叫把空气也一并割裂,如同将回忆凶狠切开。
漆面剥落,碎片像黑色雪花散落。
彻底的、无法补救的破碎,发在四人眼前,像覆水泼下地面,流向四方,不能复归。
徒留几声支离破碎的余音,在空气中发出最后的胸腔共鸣。
“不要!!!”
朱浩锋后知后觉冲过去,跪在方乐文面前、破碎的吉他旁边。
他伸出手,下意识犹豫从何处拾起这把琴,才会让它不再继续受伤,却只敢将手悬在半空中,颤抖着无从落下。
十分钟后,门再次被推开。
朱浩锋走进来,脚步带着几分不耐。
目光扫过众人时,他神色的冷意肉眼可见。
话不多说,他直接落座,低头开始组鼓。
没过多久,一串急促、硬朗到连喘息缝隙都不给的鼓点炸开——今日份的练习开始,尽管今日看起来不太平!
方乐文抱着吉他,指尖落下,旋律轻盈滑动,每一次上滑都带有倔强的锋芒。
秦阳踩下效果器,delay与phaser在空气中牵出道道虚影,将方乐文的旋律拉扯至时而犀利,时而飘忽。
周锵锵左手稳稳压住低音,像无声的暗流,往下托住音场;右手在和声中谨慎游走,试图将两把吉他的分歧收拢成循环。
就在此时——
朱浩锋的鼓棒敲进来。
节奏极简、精准,今天却沉重过头。
每一个鼓点落下,都仿佛钉子砸向地板,力道里带有明显的压迫。
旋律上升,效果器下沉,反之亦然;低音压制,留白空缺;鼓点平稳,在每个循环中惊鸿一现。
四种声音交相互交织,形成奇异的张力,紧绷却完整。
这张力,又有些难以言喻的如履薄冰。
果然,下一秒钟,薄冰碎裂。
不知为何,朱浩锋一个失神,鼓点空了半拍。
方乐文的吉他猛然旋律拉高,冲出整体,直接撞击在由于追赶而稍显急促的鼓点节奏上。
朱浩锋瞬间回击。
他眉头紧皱,军鼓砸下,节奏不仅补回,更是渐进,直接插入shuffle。
方乐文旋律再升。
朱浩锋节奏再紧。
一时间,工作室蜕变成搏斗场,弦与鼓互相顶上去,谁也不肯让步。
周锵锵立即加入pad想要救场,但他的键盘音被两股力量直接撕开,失控到火花四溅。
未免火上浇油,秦阳索性停下手中的吉他。
工作室瞬间仅剩下嘈杂的噪音与震动——
旋律像锋利的刀刃,鼓点似无情的重锤,两股力量再无调和,直接将周锵锵的键盘驱逐至无人区。
周锵锵意识到,吉他和鼓点的冲突进展到他无法调和的地步,不得已也停了下来。
这一停,总算惊醒梦中的方乐文与朱浩锋。
二人的乐器争端戛然而止,tereza工作室一度安静异常。
终于,方乐文骤然按住琴弦,琴声被他粗暴掐断。
他站起身来,咆哮声从胸腔迸裂而出,冲着朱浩锋:“你到底想怎么样?!忽快忽慢,你他妈在打什么节奏!?”
朱浩锋抬起头,放下鼓棒,眼神冷静:“我没有忽快忽慢,我的节奏从来没有变过!”
“你放屁!”
方乐文声音激烈,像硬压住某种濒临爆炸的东西。
他深呼吸一口,手指颤抖,却依旧刻意将那把黑色吉他轻轻放下。
他站起来,朝朱浩锋冲了过去,带着彻底失控的愤怒。
他一把揪住朱浩锋的衣领,将其从座位上拎了起来,力道大到他浑然不觉。
“我他妈就是——”
他吼到一半,像被逼到绝境,声音破碎,眼眶发红:“太容易相信你!”
周锵锵本能地上前拉架,秦阳紧随其后,站到他旁边。
“乐文,有话好说,你明知道浩锋对你……”
周锵锵想说些什么,让事情不至于变得更糟,却被方乐文的下一句震慑住。
“我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啊????”
方乐文一声诘问犹如惊雷,将所有压抑、委屈、期待、痛苦全部剖开,残酷地呈现在朱浩锋眼前。
那声音太响,太痛,太直接,导致朱浩锋的眼皮不受控制地轻颤一下。
猝不及防地,朱浩锋眨眼的须臾,方乐文的眼泪掉落下来。
周锵锵看得胸口发紧。
一路走来,方乐文为朱浩锋黯然神伤的太多时刻,他都陪在身边。
他为方乐文难过,也为朱浩锋难过,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们由于世事无常吃过的那些苦,他喉咙发酸,咬紧牙关。
在令人窒息的混乱中,朱浩锋没有沉默:
“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咬字极重,仿佛将心声按在每一个字上:“我四年前就告诉过你!我上周……再次回答了你!我的答案,从来没有变过!”
方乐文的呼吸紊乱,揪着朱浩锋衣领的指节发白。
头昏脑涨中,他再听朱浩锋继续说:
“只是!”
“只是现在的我……不能像四年前那样——自由、勇敢,想爱就爱,想疯就疯,在这个世界上只做自己想做的那种人!”
“我花了四年……去弥补对我妹、对我妈犯下的错误……”
“那我呢?!啊???”
朱浩锋的话没有让方乐文卸下心防,反而形同一把火铲,把他心中烧不透的、浇不净的火星全都刨出来,顷刻间点得更旺、更痛,更来势汹汹:
“你花这些年去弥补对莎莎的、对你家人的那些遗憾,那我呢!!!”
“为什么你牺牲的总是我!!!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给我希望、又丢下我???”
“你在耍我吗!!!”
方乐文歇斯底里的声线,震得整个tereza工作室嗡嗡作响,震碎周遭与世无争的空气,响彻朱浩锋和方乐文各自的,千山万水分隔两地思念疯长心气荒芜的四年。
“我没有耍你!”
朱浩锋不再对方乐文的质询讳莫如深,他眼底那层最后的冷静不复存在。
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个初初成长的青年人最真实的迷茫与彷徨。
“我也需要时间……去尝试弥补……永远弥补不了的遗憾……去身体力行宽慰家人,去独自一人舔舐伤口,去承认我远远不如自己以为的那样强大——强大到可以周全所有!”
“现在,我总算……”
“总算什么?”
方乐文胸口剧烈起伏,胸腔间有巨大悲愤:“总算在回美国之前,把我睡了?”
在场所有人,都因为这句话,怔住了。
朱浩锋显然未料到方乐文会用如此自轻自贱的方式定义两人的关系。
他眉头微蹙,眼睛睁大,看向方乐文的目光中尽是心痛与难以置信——泪光直接涌了上来。
“四年前,你吻了我,说永远不会离开我,可是你走了……”
“一周前,我稀里糊涂和你上了床,你趁我醉着,说让我等你……”
“可是我醒来后,好像一切都没发过?!是我对你欲求不满到出现幻觉的地步了吗?!”
“朱浩锋,回答我!!!你要把我当傻子玩弄到什么时候!!!”
方乐文再次揪起朱浩锋的衣领,恨意在眼底翻滚,爱意在心头涌动,如火苗附着于伤口上。
他死死盯住朱浩锋,像是要从他身上牵扯出一个解释,一个答案,一个只要对方开口、便能挽救过去整整四年的答案。
周锵锵循着方乐文的视线回头望去。
朱浩锋目不转睛注视着方乐文,他反手扣住方乐文的手臂,恳切地说:“再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毕业,我会……”
“等你毕业?等毕业时你妈再次哭着求你留在美国,求你结婚子,走阳关大道,然后你再一次把我像四年前一样丢在北城、丢在回忆里……?”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
方乐文好像疯了,边喊着,边甩开朱浩锋的双手,踉跄着冲向方才的座位。
周锵锵意识到不妙,刚想伸手阻止,已经来不及。
方乐文抓住那把黑色吉他。
——朱浩锋在远赴美国之前,为他挑选的十八岁成人礼,他最珍惜的宝贝。
指尖触碰到琴身的一刹那,整个人像过电一样僵在原地。
那一瞬太短,却足以让方乐文脑海中晃过所有闪回……
然而,须臾过后,冲动海潮般席卷而来,将所有回忆淹没到支离破碎。
方乐文的眼中闪过绝望的决绝,他举起那把吉他……
下一秒,整个工作室如被惊雷砸中。
黑色吉他狠狠摔在地上。
琴身先是错位,再爆裂——清脆、尖锐,带着绝望的残响,好似心脏被硬撕开。
琴弦同时崩断。
一根,两根,三根……
金属拉断时的尖叫把空气也一并割裂,如同将回忆凶狠切开。
漆面剥落,碎片像黑色雪花散落。
彻底的、无法补救的破碎,发在四人眼前,像覆水泼下地面,流向四方,不能复归。
徒留几声支离破碎的余音,在空气中发出最后的胸腔共鸣。
“不要!!!”
朱浩锋后知后觉冲过去,跪在方乐文面前、破碎的吉他旁边。
他伸出手,下意识犹豫从何处拾起这把琴,才会让它不再继续受伤,却只敢将手悬在半空中,颤抖着无从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