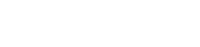“小奇,你,你怎么不吃?”
周锵锵虽憨,但也没有那么憨,他赶忙抄起一张纸巾,尴尬地替自己擦擦嘴,关切问询。
杨霁一言难尽:“看你们吃这么香,我可能饱了……”
那之后,五人边吃边聊了一个小时,聊起音乐,谈话总算渐入佳境。
周锵锵之前就告知过杨霁,他们四人相识于高中,以音乐为契机走到一起。
这次见面,周锵锵则补充,他们目前共同成立了一支乐队,不时到各大音乐节和livehouse露面演出。
杨霁随口一问:“乐队的名字?”
周锵锵窒息了——他差点忘记,数字时代,人在搜索引擎面前早已无所遁形。
适逢此时,方乐文洞悉一切,出来补位:“莎莎。”
“莎莎”二字既出,场上的气氛忽而沉寂。
方乐文斜瞥到朱浩锋身上,朱浩锋有一刹那尤其焦躁,看向方乐文,似是有话要说,终究还是咽了回去。
杨霁在美国两年出入各种饭局酒局,回国后一路高歌猛进不到三十岁便做到中层,基本的察言观色能力无疑很是出色。
他注意到四人之间没心没肺的相处模式,猝不及防由于简单的“莎莎”二字便大打折扣,料定乐队成立必然有一段不轻易为外人道的典故。
杨霁也不追问,而是掏出手机,作势看一眼时间,开口写下休止符:
“一会儿就要上班了,我从这里赶回公……单位,时间充裕的话需要半小时,谢谢周老师今天款待,谢谢诸位分享音乐故事,我下次再请各位吃饭!”
第19章 慢:渐强(1)
从必客走出来,与tereza的兄弟三人分道扬镳,周锵锵提议,送杨霁去他的单位。
杨霁心底也有盘算,掐指一算离上班时间尚有一小时,便问:“要不到简单喝杯咖啡?”
周锵锵听见提议,思忖片刻,摇了摇头:“不好,不浪漫。”
杨霁无语:“这大中午的,全城人民都在为计奋斗,你在这里何不食肉糜做什么?”
周锵锵要是能被杨霁嘲讽到就不叫周锵锵,他毫无征兆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右手牵起杨霁的左手,说:“你跟我来,我带你去我高中很喜欢的地方!”
杨霁想提醒周锵锵:我们好像没有很熟,你怎么就如此光天化日之下牵我的手?
话才到嘴边,便被周锵锵一股亢奋的怪力牵着往前方……的公交站牌奔去。
“小奇,你的单位在哪个方向?是往市中心吗?”二人到达公交站牌后,周锵锵问。
杨霁有些欲言又止,半晌,还是随口胡诌:“坐353能到。”
周锵锵一听353,立即双眼亮了!
一抬头,来的正是一辆353,还是双层车,有情饮水饱指数拉满了!
“跟我来!”周锵锵不由分说再次牵起杨霁的手。
“老哥,你……”
杨霁从无语到失语,未免使得周锵锵在众目睽睽下更为醒目,他只得硬着头皮跟随周锵锵上车。
果真如杨霁所说,夜幕尚未降临,全程人民还在辛劳奔走,所以353内人丁稀少。
周锵锵喜出望外地扯着杨霁的手上了二楼。
好家伙!双层车的精华宝座第一排,空空如也!
周锵锵像刚从麻将桌上问吝啬的老父亲拿到零花钱一样,高兴得像个二十出头的男大。
他招呼杨霁坐在座位内侧,方便观景,自己则坐在靠走廊处。
杨霁费解:“不是,这景,有什么可观的?这不是你我平平无奇看了二三十年的普通北城吗?”
周锵锵谬论一套接一套:“不对。你想想,达芬奇的蛋都有千百颗不同形态,我们的北城,怎么能天天一样呢?”
说着,周锵锵专注地盯着窗外,抬手指向窗外西北方向,对杨霁说:“你看,此时此刻的北城永安大街,有一位三十岁上下的男子,骑着他的小电动车,驮着一大袋气球,气球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亮出耀眼的红颜色。”
“可人家不这么想,人家只想着今晚这些气球不卖完,今日份kpi卒。”杨霁毫不留情泼冷水。
“也不一定。”周锵锵似有不同看法:“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他继续说:“像小奇你这样从小到大都很优秀的精英,总觉得人间正路仅有那一条通天大道,可是,也许个人有个人的活法……我不是刻意要浪漫化这个世界,而是,世间道路千万条,我们又怎知道,他人的羊肠小道不能通往他人的桃源乡呢?”
杨霁在周锵锵的质询下,回想片刻,发现自己人鲜少与这种怀抱着八百吨罗曼蒂克呱呱落地的人深入交谈,故而也从未陷入这种语塞,除了……
除了大学时期,以一种极其幼稚的姿态与父母争取自由和权利。
那时的他一如当下的周锵锵——可现在的他有些困惑,这些形而上的虚无,讨论的结果究竟能是什么呢?
杨霁闭上眼,察觉到太阳穴处有规律地跳动,烈日当空,有些头疼。
也许周锵锵也意识到谈话陷入窘境,也许没有,只是他问:“小奇,你在哪一站下车?”
杨霁随口拣了个站点脱口而出:“灵犀路。”
周锵锵兴高采烈:“那敢情好,我们在灵犀路的前一站槐街口路下车,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杨霁奇怪,这货怎么如此活力四射,拜托,我们刚才不是还在话不投机?
可周锵锵不管,灵犀路前一站,槐街口路抵达报站,周锵锵再次牵起杨霁的手:“走,我们到了。”
杨霁被牵手牵得没脾气,他心想,只要这货别再消耗我的脑细胞,他想怎样就怎样吧。
杨霁跟随周锵锵下了车。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钢筋混凝土天地,十余幢摩天大楼此起彼伏,好一派整齐划一的现代城市景观。
只是,曾经蜿蜒绵长伸入梦境的胡同,如今已成被铲平的荒地,被遮掩于落地窗折射在地面的强光当中。
微风轻拂,拂过看得见的回不去的街角,拂向遥远的时间。
窄小的门楣,斑驳的玻璃,投在架子上密密麻麻的磁带、黑胶唱片,打口儿碟片,半帘阳光透入,窗帘每飘起一次,便让人昏昏沉浮想联翩,也许那片帘后藏着命定的少年。
不经意地,杨霁的手被周锵锵再次牵起,将他从愣神的片刻轻轻牵扯,醒在这个温暖的午后,周锵锵的身旁。
“高中的时候……迷茫于熙熙攘攘的人间正道,和看起来特别缥缈的理想,音乐。很幸运地,像陶渊明坐船驶向桃花源一般,在隐蔽的槐影胡同里找到了范哥的音像店,encounter,从而慰藉了我高中的茫然失措。”
杨霁没有轻易接话,而是随着周锵锵的节奏,抬腿渐渐朝纵深走去——这里的人已经渐渐搬空,从过去人声鼎沸遍地市井气息,到现在满目凋敝。
闭上眼睛,杨霁仿佛还能看见背着双肩书包的高中大学,骑着滑板车在狭窄的胡同中来回穿梭,只为那一下午被缪斯女神轻抚面颊,从而褪去一周庸碌疲乏。
原来,不止他一个人为这座城市里变为废墟的乐土伤春悲秋过,只是即便当他从美国归来,即便靠得如此近,如果不是周锵锵,他再也没有踏入过这里。
他的决绝一如他当初二话不说远走高飞,一如他将尘封的旧过往一并打包,丢进断舍离大军,丢进回不去的记忆里。
原来,少年曾来过同一个梦中。
“小奇?”周锵锵歪头凑近端详。
杨霁回过神来,却听周锵锵问:“你有没有听见?有人练钢琴的声音?”
当年此处人丁兴旺,大量市中心的多代同堂老居民在这里坐落。
城市进入大规模改造后,绝大部分人得到了大笔拆迁款,并搬离了出成长的地方,被疏散至四环开外,只零零星星尚有人散居于此。
隐隐约约传出的练习曲,好像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慢板,柔和,伴随着并不熟练的指尖运动与不时出错的音阶。
周锵锵和杨霁漫步在胡同当中,在现下一片稀疏的民居中,找寻那练琴声音究竟来自何方,最终,在一间看得出主人悉心装点过的宅院停下。
“没想到现在还有人在这儿练这个。我小时候也练过,一边练,一边挨打,错一个音打一下手。”杨霁轻笑一声,回想道。
周锵锵也有话要说:“我也练过,小时候弹得一塌糊涂,老弹错节拍,我妈边敷面膜边帮我踩着拍子,人比我还着急。”
杨霁想象一下,周锵锵这淡定自若的个性,的确能让周围所有人皇帝不急太监急,他忍俊不禁,附和:“我小时候弹到中间那一段,总是弹不过去,差点没被我妈打成肉饼。”
周锵锵忙不迭:“我也是我也是!每次弹到那儿,我都以为自己做不到了!”
“但是……”
周锵锵继续说,笑嘻嘻露出两个大酒窝,在阳光底下格外耀眼:“但是,我们都还是弹过去了。”
周锵锵虽憨,但也没有那么憨,他赶忙抄起一张纸巾,尴尬地替自己擦擦嘴,关切问询。
杨霁一言难尽:“看你们吃这么香,我可能饱了……”
那之后,五人边吃边聊了一个小时,聊起音乐,谈话总算渐入佳境。
周锵锵之前就告知过杨霁,他们四人相识于高中,以音乐为契机走到一起。
这次见面,周锵锵则补充,他们目前共同成立了一支乐队,不时到各大音乐节和livehouse露面演出。
杨霁随口一问:“乐队的名字?”
周锵锵窒息了——他差点忘记,数字时代,人在搜索引擎面前早已无所遁形。
适逢此时,方乐文洞悉一切,出来补位:“莎莎。”
“莎莎”二字既出,场上的气氛忽而沉寂。
方乐文斜瞥到朱浩锋身上,朱浩锋有一刹那尤其焦躁,看向方乐文,似是有话要说,终究还是咽了回去。
杨霁在美国两年出入各种饭局酒局,回国后一路高歌猛进不到三十岁便做到中层,基本的察言观色能力无疑很是出色。
他注意到四人之间没心没肺的相处模式,猝不及防由于简单的“莎莎”二字便大打折扣,料定乐队成立必然有一段不轻易为外人道的典故。
杨霁也不追问,而是掏出手机,作势看一眼时间,开口写下休止符:
“一会儿就要上班了,我从这里赶回公……单位,时间充裕的话需要半小时,谢谢周老师今天款待,谢谢诸位分享音乐故事,我下次再请各位吃饭!”
第19章 慢:渐强(1)
从必客走出来,与tereza的兄弟三人分道扬镳,周锵锵提议,送杨霁去他的单位。
杨霁心底也有盘算,掐指一算离上班时间尚有一小时,便问:“要不到简单喝杯咖啡?”
周锵锵听见提议,思忖片刻,摇了摇头:“不好,不浪漫。”
杨霁无语:“这大中午的,全城人民都在为计奋斗,你在这里何不食肉糜做什么?”
周锵锵要是能被杨霁嘲讽到就不叫周锵锵,他毫无征兆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右手牵起杨霁的左手,说:“你跟我来,我带你去我高中很喜欢的地方!”
杨霁想提醒周锵锵:我们好像没有很熟,你怎么就如此光天化日之下牵我的手?
话才到嘴边,便被周锵锵一股亢奋的怪力牵着往前方……的公交站牌奔去。
“小奇,你的单位在哪个方向?是往市中心吗?”二人到达公交站牌后,周锵锵问。
杨霁有些欲言又止,半晌,还是随口胡诌:“坐353能到。”
周锵锵一听353,立即双眼亮了!
一抬头,来的正是一辆353,还是双层车,有情饮水饱指数拉满了!
“跟我来!”周锵锵不由分说再次牵起杨霁的手。
“老哥,你……”
杨霁从无语到失语,未免使得周锵锵在众目睽睽下更为醒目,他只得硬着头皮跟随周锵锵上车。
果真如杨霁所说,夜幕尚未降临,全程人民还在辛劳奔走,所以353内人丁稀少。
周锵锵喜出望外地扯着杨霁的手上了二楼。
好家伙!双层车的精华宝座第一排,空空如也!
周锵锵像刚从麻将桌上问吝啬的老父亲拿到零花钱一样,高兴得像个二十出头的男大。
他招呼杨霁坐在座位内侧,方便观景,自己则坐在靠走廊处。
杨霁费解:“不是,这景,有什么可观的?这不是你我平平无奇看了二三十年的普通北城吗?”
周锵锵谬论一套接一套:“不对。你想想,达芬奇的蛋都有千百颗不同形态,我们的北城,怎么能天天一样呢?”
说着,周锵锵专注地盯着窗外,抬手指向窗外西北方向,对杨霁说:“你看,此时此刻的北城永安大街,有一位三十岁上下的男子,骑着他的小电动车,驮着一大袋气球,气球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亮出耀眼的红颜色。”
“可人家不这么想,人家只想着今晚这些气球不卖完,今日份kpi卒。”杨霁毫不留情泼冷水。
“也不一定。”周锵锵似有不同看法:“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他继续说:“像小奇你这样从小到大都很优秀的精英,总觉得人间正路仅有那一条通天大道,可是,也许个人有个人的活法……我不是刻意要浪漫化这个世界,而是,世间道路千万条,我们又怎知道,他人的羊肠小道不能通往他人的桃源乡呢?”
杨霁在周锵锵的质询下,回想片刻,发现自己人鲜少与这种怀抱着八百吨罗曼蒂克呱呱落地的人深入交谈,故而也从未陷入这种语塞,除了……
除了大学时期,以一种极其幼稚的姿态与父母争取自由和权利。
那时的他一如当下的周锵锵——可现在的他有些困惑,这些形而上的虚无,讨论的结果究竟能是什么呢?
杨霁闭上眼,察觉到太阳穴处有规律地跳动,烈日当空,有些头疼。
也许周锵锵也意识到谈话陷入窘境,也许没有,只是他问:“小奇,你在哪一站下车?”
杨霁随口拣了个站点脱口而出:“灵犀路。”
周锵锵兴高采烈:“那敢情好,我们在灵犀路的前一站槐街口路下车,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杨霁奇怪,这货怎么如此活力四射,拜托,我们刚才不是还在话不投机?
可周锵锵不管,灵犀路前一站,槐街口路抵达报站,周锵锵再次牵起杨霁的手:“走,我们到了。”
杨霁被牵手牵得没脾气,他心想,只要这货别再消耗我的脑细胞,他想怎样就怎样吧。
杨霁跟随周锵锵下了车。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钢筋混凝土天地,十余幢摩天大楼此起彼伏,好一派整齐划一的现代城市景观。
只是,曾经蜿蜒绵长伸入梦境的胡同,如今已成被铲平的荒地,被遮掩于落地窗折射在地面的强光当中。
微风轻拂,拂过看得见的回不去的街角,拂向遥远的时间。
窄小的门楣,斑驳的玻璃,投在架子上密密麻麻的磁带、黑胶唱片,打口儿碟片,半帘阳光透入,窗帘每飘起一次,便让人昏昏沉浮想联翩,也许那片帘后藏着命定的少年。
不经意地,杨霁的手被周锵锵再次牵起,将他从愣神的片刻轻轻牵扯,醒在这个温暖的午后,周锵锵的身旁。
“高中的时候……迷茫于熙熙攘攘的人间正道,和看起来特别缥缈的理想,音乐。很幸运地,像陶渊明坐船驶向桃花源一般,在隐蔽的槐影胡同里找到了范哥的音像店,encounter,从而慰藉了我高中的茫然失措。”
杨霁没有轻易接话,而是随着周锵锵的节奏,抬腿渐渐朝纵深走去——这里的人已经渐渐搬空,从过去人声鼎沸遍地市井气息,到现在满目凋敝。
闭上眼睛,杨霁仿佛还能看见背着双肩书包的高中大学,骑着滑板车在狭窄的胡同中来回穿梭,只为那一下午被缪斯女神轻抚面颊,从而褪去一周庸碌疲乏。
原来,不止他一个人为这座城市里变为废墟的乐土伤春悲秋过,只是即便当他从美国归来,即便靠得如此近,如果不是周锵锵,他再也没有踏入过这里。
他的决绝一如他当初二话不说远走高飞,一如他将尘封的旧过往一并打包,丢进断舍离大军,丢进回不去的记忆里。
原来,少年曾来过同一个梦中。
“小奇?”周锵锵歪头凑近端详。
杨霁回过神来,却听周锵锵问:“你有没有听见?有人练钢琴的声音?”
当年此处人丁兴旺,大量市中心的多代同堂老居民在这里坐落。
城市进入大规模改造后,绝大部分人得到了大笔拆迁款,并搬离了出成长的地方,被疏散至四环开外,只零零星星尚有人散居于此。
隐隐约约传出的练习曲,好像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慢板,柔和,伴随着并不熟练的指尖运动与不时出错的音阶。
周锵锵和杨霁漫步在胡同当中,在现下一片稀疏的民居中,找寻那练琴声音究竟来自何方,最终,在一间看得出主人悉心装点过的宅院停下。
“没想到现在还有人在这儿练这个。我小时候也练过,一边练,一边挨打,错一个音打一下手。”杨霁轻笑一声,回想道。
周锵锵也有话要说:“我也练过,小时候弹得一塌糊涂,老弹错节拍,我妈边敷面膜边帮我踩着拍子,人比我还着急。”
杨霁想象一下,周锵锵这淡定自若的个性,的确能让周围所有人皇帝不急太监急,他忍俊不禁,附和:“我小时候弹到中间那一段,总是弹不过去,差点没被我妈打成肉饼。”
周锵锵忙不迭:“我也是我也是!每次弹到那儿,我都以为自己做不到了!”
“但是……”
周锵锵继续说,笑嘻嘻露出两个大酒窝,在阳光底下格外耀眼:“但是,我们都还是弹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