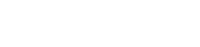然而,现实容不下半分温情。
被保镖隔开的媒体嗅到了异样的空气,闪光灯更加疯狂地闪烁。
蒲子骞眼中汹涌的情绪瞬间冻结,本能地充满戒备,更不愿再提起过往伤痕。他别过头,避开纪岑林眼中那一闪而过的惊痛。
就在这时,“嘀——”
一声清晰的电子音,从急救室方向传来。
急救室门顶刺目的红灯倏然熄灭,取而代之的是象征着未知的绿灯。
时间仿佛忽然按下暂停键。
那些愤怒的、疲惫的、探究的、贪婪的目光,全都聚焦在那扇缓缓开启的门缝上。
走廊死寂无声,唯有蒲子骞和纪岑林急促的心跳,以及曾经响彻在彼此青春岁月里的摇滚巨响,在无声地对峙与交织。
那道声浪仿佛带着旧日音箱的震动,廉价啤酒的泡沫气息,汗水和泪水混合的咸涩,以及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与梦想,沉重地砸在耳膜上,砸在心上,砸在这片冰冷现实的废墟之上。
让他们痛着,却不愿醒来。
第11章 不同图层
当飞虫在路灯下弹撞开来,specialized越野自行车在林荫道留下一道疾驰的身影——它的主人17岁,正弓着背脊,穿梭于校园。
纪岑林脖子上挂着头戴式耳机,身穿白色t恤,外面套了件银灰色皮肤衣,雨渍在手臂透出肌理。今天他是临时过来的,短信通知他上周的面试通过,他要正式成为乐队的键盘手了,说实话,乐队叫什么名儿他全忘了。
准确来讲,他追随的不是小众乐队,而是小众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蒲子骞。
这哥是隔壁深涌音乐学院的,跟他一样,今年刚大一,却在一入校,就引起不少轰动。深涌音乐学院也叫‘deepmusicartuniversity’,常被称为dmau,在全国音乐学院里至少能排进前五。
至于蒲子骞为何刚入校就引起轰动,纪岑林用脚趾头也想得出来,无非是人帅,歌儿唱的又好,毕竟大一就能在livehouse搞演出,是有点牛逼在身上。
纪岑林就读于音乐学院旁边的一所重点综合性大学,专业跟念经一样让他讨厌,该死的金融学管理,简直无聊透顶。再不出来透风,纪岑林觉得自己一定会发霉。
见面地点约深涌音乐学院西南校门口。
纪岑林是从自己学校一路骑过来的,出了校园,他又沿着公路继续骑行了几公里,红绿灯切换,车身轻跃着冲过天桥,长坡近在眼前,他松开手刹俯冲而下。
很快,纪岑林从人群中锁住一个身影,太晃眼了——蒲子骞很高,正站在公交站廊檐下躲雨,身穿工字型背心,外面套了件棉麻衬衫,有线耳机线蛇行于他的锁骨,吉他包勒出肩胛锐角。他的头发蓬松,也有些凌乱,好像烫过,是很自然的弧度。
蒲子骞的手指切换至微信页面,给一个名叫c-lin的微信用户发了条信息:到了吗。
公交车车身摇晃着驶离时,纪岑林已刹停在他面前。
蒲子骞跟他打了个招呼,“嘿!”
“这是纪岑林。”蒲子骞侧过脸,像是在跟谁介绍他,声音很轻:“之前跟你说过的。”
纪岑林这才注意到蒲子骞身边还站了一个人,看着很面,人瘦瘦的,个子不矮,估计也有850,就是站在857的蒲子骞旁边,显得有点瘦弱,很单薄的一个人,不像蒲子骞身上还有肌肉。
“我们的贝斯手,周千悟。”蒲子骞笑了笑,话是对纪岑林说的:“正好认识一下。”
名叫周千悟的男终于抬头,纪岑林看到一双清澈的眼睛,不太爱笑的眉宇,下巴瘦瘦的,穿着干净而宽大的灰色t恤。他像是突然从蒲子骞影子里剥离出来的暗色水痕,帆布鞋边还沾着半片榕树气根,他真的很像贝斯,安静而低调,却是音律中不可缺少的低频律动。
上次演出也有贝斯手吗?可能低频藏在副歌里,当时光顾着去听蒲子骞唱歌了,没有留意到贝斯手吧,纪岑林心想。
“你好,”纪岑林自我介绍,“纪岑林。”
周千悟笑了一下,但也是淡淡的。
三个人往商业街方向走,蒲子骞注意到纪岑林的越野自行车,“车不错,抓地感很强吧?”
纪岑林单手抓握着车把,手臂上青筋清晰可见,“还行。”
周千悟站在蒲子骞的另一边,偏头看了一下,问:“怎么不锁上,前面就是步行街了,人很多。”
纪岑林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蒲子骞偏了偏头,细心解释:“这种车不用锁。”
“为什么,”周千悟收起蓝牙耳机,“不怕被偷吗。”
蒲子骞说:“好车不用锁,因为走哪儿都得带着,用再好的锁也会被偷。”
“噢。”周千悟这才真正笑了一下,纪岑林用余光留意到周千悟微不可见的雀跃。
过了一会儿,纪岑林松开一只手,问周千悟:“你要试试吗。”
周千悟腼腆地摆手,“不用了。”
人渐渐多了起来,三个原本并排走的人,不得不前后错开,纪岑林单手推着车,稍微等了一下,蒲子骞紧跟在他右手边,只有周千悟走在最后。
人潮裹挟的瞬间,周千悟险些踉跄,为了避让行人,他不小心触碰到纪岑林的手臂,又触电般地移开。
纪岑林跟蒲子骞差不多高,他侧过脸去看周千悟,周千悟只沉默地把双手扁在背后。手臂上残留的凉意蜿蜒向上,让纪岑林觉得贝斯手的体温,好像也比普通人要低。
正说着,蒲子骞接了个电话,“都到了,就差你,”他往四周看了看,“赶紧的,别让人等。”
蒲子骞跟这个人说话不拘小节,但面对周千悟,他的声音像吉他扫弦后的弱音,纪岑林好奇地看向他,蒲子骞淡然一笑,“还有个打鼓的,吴道,我们都叫他阿道,你也可以叫他道哥。”
他们要去商业街的乐器行,‘老郑乐器行’不知不觉间近在眼前,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吉他,还有二胡、小提琴,架子鼓放在更里面的位置。
玻璃门即将推开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风风火火的声音:“老子真服了,实践课给我整到现在,电驴钥匙又丢了,回去也没找到,拿着拿着——”说着,四杯西瓜汁凑了上来,全都塞到蒲子骞手上。
纪岑林定眼一看,是个年纪相仿的男,微壮,肤色偏黑,寸头,胡子拉碴。
门口上方的铃铛轻响了一下,里面传来一道声音,“哟,快请进,里边有冷气!”应该是老板。
蒲子骞没有着急进去,朝阿道扫了一眼,嘴角带笑,有几分玩味的意思:“又挨你老子叼了?”
“别提他!”阿道臊眉搭眼的,满脸晦气,没好气地挥手:“他就见不得我打鼓,成天想把我轰出去,”说着,他又瞄向蒲子骞身后,眉眼一挤,不怀好意道:“小周呢?”
蒲子骞眉毛微皱了一下。
周千悟从蒲子骞身后冒出来,朝阿道翻了个白眼,阿道顿时又气又笑,“你小子手又好了?你就能吧,也就骞哥护着你!”说的是上回搬宿舍砸到手那件事。
好在伤得不重,蒲子骞的脸色难看了好几个星期。
“进去吧?”蒲子骞推开门,抬了抬下巴,“上次不是说鼓槌坏了吗。”
阿道忙不迭跟在蒲子骞身后,还朝周千悟递了个眼色,示意他一起进来。
周千悟摇头:“里面太冷了,我就在外面。”
“娇气。”阿道拉下脸,作势要敲周千悟的脑袋,周千悟赶忙把玻璃门关上,隔着玻璃门对着阿道张牙舞爪,不知道一个人在那儿傻乐什么。
纪岑林这才注意到周千悟是会开玩笑的,只是因为跟自己不熟,所以显得话格外少。他跨坐在单车上,长脚支地,时不时看看手机,又留意自己有没有挡住来往的路人。
结账的时候,阿道本想自己扫码,蒲子骞推开他的手机,“一起算。”
老板问蒲子骞最近有没有换琴的打算,蒲子骞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还跟阿道提了一句:“人凑齐了。”
乐队里一直缺键盘手,之前几个要么是技术不行,要么就是光顾着谈恋爱,搞得蒲子骞很烦躁,这事儿阿道很清楚,“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亏得我买了四杯果汁。”
“你没看见?”蒲子骞忽然抬起眼眸,一脸不可置信。
“你也没介绍啊!”
蒲子骞真服了,他拿着新买的吉他弦,往不远处一指:“那不是吗?”
阿道顺着蒲子骞的手看过去,玻璃门外行走着许多人,只有两个人是静默着等待的。斜对面的洗头灯把地面照得五彩斑斓,落在年轻男孩的白色t恤背后,年轻男孩留着美式刺头,侧脸英挺,单手撑在车把上,弓着背,背脊线绷紧,整个人像只亚成年雄狮。他好像在打游戏,另一只脚踩在台阶上,一前一后地蹬着。车子好炫,跟周遭的市井气息格格不入。
而另一边的周千悟,斜挎着背包,抬头望向头顶的白炽灯附近的飞虫,像是阅读五线谱上休止符的诗人。室内光线足,蒲子骞半透明的身影映在玻璃上,三个人像是印在同一张照片的不同图层。
被保镖隔开的媒体嗅到了异样的空气,闪光灯更加疯狂地闪烁。
蒲子骞眼中汹涌的情绪瞬间冻结,本能地充满戒备,更不愿再提起过往伤痕。他别过头,避开纪岑林眼中那一闪而过的惊痛。
就在这时,“嘀——”
一声清晰的电子音,从急救室方向传来。
急救室门顶刺目的红灯倏然熄灭,取而代之的是象征着未知的绿灯。
时间仿佛忽然按下暂停键。
那些愤怒的、疲惫的、探究的、贪婪的目光,全都聚焦在那扇缓缓开启的门缝上。
走廊死寂无声,唯有蒲子骞和纪岑林急促的心跳,以及曾经响彻在彼此青春岁月里的摇滚巨响,在无声地对峙与交织。
那道声浪仿佛带着旧日音箱的震动,廉价啤酒的泡沫气息,汗水和泪水混合的咸涩,以及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与梦想,沉重地砸在耳膜上,砸在心上,砸在这片冰冷现实的废墟之上。
让他们痛着,却不愿醒来。
第11章 不同图层
当飞虫在路灯下弹撞开来,specialized越野自行车在林荫道留下一道疾驰的身影——它的主人17岁,正弓着背脊,穿梭于校园。
纪岑林脖子上挂着头戴式耳机,身穿白色t恤,外面套了件银灰色皮肤衣,雨渍在手臂透出肌理。今天他是临时过来的,短信通知他上周的面试通过,他要正式成为乐队的键盘手了,说实话,乐队叫什么名儿他全忘了。
准确来讲,他追随的不是小众乐队,而是小众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蒲子骞。
这哥是隔壁深涌音乐学院的,跟他一样,今年刚大一,却在一入校,就引起不少轰动。深涌音乐学院也叫‘deepmusicartuniversity’,常被称为dmau,在全国音乐学院里至少能排进前五。
至于蒲子骞为何刚入校就引起轰动,纪岑林用脚趾头也想得出来,无非是人帅,歌儿唱的又好,毕竟大一就能在livehouse搞演出,是有点牛逼在身上。
纪岑林就读于音乐学院旁边的一所重点综合性大学,专业跟念经一样让他讨厌,该死的金融学管理,简直无聊透顶。再不出来透风,纪岑林觉得自己一定会发霉。
见面地点约深涌音乐学院西南校门口。
纪岑林是从自己学校一路骑过来的,出了校园,他又沿着公路继续骑行了几公里,红绿灯切换,车身轻跃着冲过天桥,长坡近在眼前,他松开手刹俯冲而下。
很快,纪岑林从人群中锁住一个身影,太晃眼了——蒲子骞很高,正站在公交站廊檐下躲雨,身穿工字型背心,外面套了件棉麻衬衫,有线耳机线蛇行于他的锁骨,吉他包勒出肩胛锐角。他的头发蓬松,也有些凌乱,好像烫过,是很自然的弧度。
蒲子骞的手指切换至微信页面,给一个名叫c-lin的微信用户发了条信息:到了吗。
公交车车身摇晃着驶离时,纪岑林已刹停在他面前。
蒲子骞跟他打了个招呼,“嘿!”
“这是纪岑林。”蒲子骞侧过脸,像是在跟谁介绍他,声音很轻:“之前跟你说过的。”
纪岑林这才注意到蒲子骞身边还站了一个人,看着很面,人瘦瘦的,个子不矮,估计也有850,就是站在857的蒲子骞旁边,显得有点瘦弱,很单薄的一个人,不像蒲子骞身上还有肌肉。
“我们的贝斯手,周千悟。”蒲子骞笑了笑,话是对纪岑林说的:“正好认识一下。”
名叫周千悟的男终于抬头,纪岑林看到一双清澈的眼睛,不太爱笑的眉宇,下巴瘦瘦的,穿着干净而宽大的灰色t恤。他像是突然从蒲子骞影子里剥离出来的暗色水痕,帆布鞋边还沾着半片榕树气根,他真的很像贝斯,安静而低调,却是音律中不可缺少的低频律动。
上次演出也有贝斯手吗?可能低频藏在副歌里,当时光顾着去听蒲子骞唱歌了,没有留意到贝斯手吧,纪岑林心想。
“你好,”纪岑林自我介绍,“纪岑林。”
周千悟笑了一下,但也是淡淡的。
三个人往商业街方向走,蒲子骞注意到纪岑林的越野自行车,“车不错,抓地感很强吧?”
纪岑林单手抓握着车把,手臂上青筋清晰可见,“还行。”
周千悟站在蒲子骞的另一边,偏头看了一下,问:“怎么不锁上,前面就是步行街了,人很多。”
纪岑林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蒲子骞偏了偏头,细心解释:“这种车不用锁。”
“为什么,”周千悟收起蓝牙耳机,“不怕被偷吗。”
蒲子骞说:“好车不用锁,因为走哪儿都得带着,用再好的锁也会被偷。”
“噢。”周千悟这才真正笑了一下,纪岑林用余光留意到周千悟微不可见的雀跃。
过了一会儿,纪岑林松开一只手,问周千悟:“你要试试吗。”
周千悟腼腆地摆手,“不用了。”
人渐渐多了起来,三个原本并排走的人,不得不前后错开,纪岑林单手推着车,稍微等了一下,蒲子骞紧跟在他右手边,只有周千悟走在最后。
人潮裹挟的瞬间,周千悟险些踉跄,为了避让行人,他不小心触碰到纪岑林的手臂,又触电般地移开。
纪岑林跟蒲子骞差不多高,他侧过脸去看周千悟,周千悟只沉默地把双手扁在背后。手臂上残留的凉意蜿蜒向上,让纪岑林觉得贝斯手的体温,好像也比普通人要低。
正说着,蒲子骞接了个电话,“都到了,就差你,”他往四周看了看,“赶紧的,别让人等。”
蒲子骞跟这个人说话不拘小节,但面对周千悟,他的声音像吉他扫弦后的弱音,纪岑林好奇地看向他,蒲子骞淡然一笑,“还有个打鼓的,吴道,我们都叫他阿道,你也可以叫他道哥。”
他们要去商业街的乐器行,‘老郑乐器行’不知不觉间近在眼前,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吉他,还有二胡、小提琴,架子鼓放在更里面的位置。
玻璃门即将推开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风风火火的声音:“老子真服了,实践课给我整到现在,电驴钥匙又丢了,回去也没找到,拿着拿着——”说着,四杯西瓜汁凑了上来,全都塞到蒲子骞手上。
纪岑林定眼一看,是个年纪相仿的男,微壮,肤色偏黑,寸头,胡子拉碴。
门口上方的铃铛轻响了一下,里面传来一道声音,“哟,快请进,里边有冷气!”应该是老板。
蒲子骞没有着急进去,朝阿道扫了一眼,嘴角带笑,有几分玩味的意思:“又挨你老子叼了?”
“别提他!”阿道臊眉搭眼的,满脸晦气,没好气地挥手:“他就见不得我打鼓,成天想把我轰出去,”说着,他又瞄向蒲子骞身后,眉眼一挤,不怀好意道:“小周呢?”
蒲子骞眉毛微皱了一下。
周千悟从蒲子骞身后冒出来,朝阿道翻了个白眼,阿道顿时又气又笑,“你小子手又好了?你就能吧,也就骞哥护着你!”说的是上回搬宿舍砸到手那件事。
好在伤得不重,蒲子骞的脸色难看了好几个星期。
“进去吧?”蒲子骞推开门,抬了抬下巴,“上次不是说鼓槌坏了吗。”
阿道忙不迭跟在蒲子骞身后,还朝周千悟递了个眼色,示意他一起进来。
周千悟摇头:“里面太冷了,我就在外面。”
“娇气。”阿道拉下脸,作势要敲周千悟的脑袋,周千悟赶忙把玻璃门关上,隔着玻璃门对着阿道张牙舞爪,不知道一个人在那儿傻乐什么。
纪岑林这才注意到周千悟是会开玩笑的,只是因为跟自己不熟,所以显得话格外少。他跨坐在单车上,长脚支地,时不时看看手机,又留意自己有没有挡住来往的路人。
结账的时候,阿道本想自己扫码,蒲子骞推开他的手机,“一起算。”
老板问蒲子骞最近有没有换琴的打算,蒲子骞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还跟阿道提了一句:“人凑齐了。”
乐队里一直缺键盘手,之前几个要么是技术不行,要么就是光顾着谈恋爱,搞得蒲子骞很烦躁,这事儿阿道很清楚,“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亏得我买了四杯果汁。”
“你没看见?”蒲子骞忽然抬起眼眸,一脸不可置信。
“你也没介绍啊!”
蒲子骞真服了,他拿着新买的吉他弦,往不远处一指:“那不是吗?”
阿道顺着蒲子骞的手看过去,玻璃门外行走着许多人,只有两个人是静默着等待的。斜对面的洗头灯把地面照得五彩斑斓,落在年轻男孩的白色t恤背后,年轻男孩留着美式刺头,侧脸英挺,单手撑在车把上,弓着背,背脊线绷紧,整个人像只亚成年雄狮。他好像在打游戏,另一只脚踩在台阶上,一前一后地蹬着。车子好炫,跟周遭的市井气息格格不入。
而另一边的周千悟,斜挎着背包,抬头望向头顶的白炽灯附近的飞虫,像是阅读五线谱上休止符的诗人。室内光线足,蒲子骞半透明的身影映在玻璃上,三个人像是印在同一张照片的不同图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