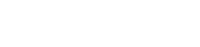外面一个人也没有。
今日来的匆忙。
没人料到这场雪。
……不知道这么冷的夜,殷管家有没有挨冻,有没有添衣?
【作者有话说】
上一章谁说的?
不得不承认,老爷似乎真有点绿帽癖?
第20章 老爷不在家
我家五个孩子。
我是老大。
我爹在外面找了份工,早早带着我娘外出讨生活。
我从小是由奶奶抚养大,与父母之间没有多少感情……后来就陆陆续续有了弟妹,奶奶老了,我便养家。
五岁的时候就会做饭,六岁可以上山砍柴。
每年最盼望的事,就是过年的时候能吃上一口肉,穿上一件新衣。可家里太穷,父母说我是老大,便从来不给我裁衣服。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幺弟幺妹是每年都有新衣的。
最早的几年,阿奶还活着,刚入腊月就把一年到头攒的点银子换了花线,接些女工活计,攒一些零钱,赶着腊八前扯一块布料,给我做件衣服。
晚上舍不得点灯。
阿奶就着风雪,在月光下赶工。
她活着的最后一年,已经看不清东西,赶不出多少女工,只能赚得一点点钱,给我做了一件马甲。
除夕那天,阿奶病得重了,躺在床上,把那件马甲让我穿上。
她眯着眼笑着说:“我们家淼淼是真好看,像是大户人家的少爷。”
“等开春奶奶病好了,再给你加袖子。”她又说。
可她没等到春天。
我也没有。
初一早晨她便咽了气,初二的时候,我爹用我换了一袋米,还有一块肉。
锅里肉刚炖烂的时候,我就被人牙子带走,卖入了香旖院。
又被茅成文看上,养在了后宅。
从此,穿上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只是这些衣服最后都没什么好下场,撕开的,被揉皱的,成了浪荡的注脚。
而春节……
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春节的。
茅家大太太对我们管教严苛,身上没有一分余钱。
茅成文和他的妻妾们团年后,会送一份冷掉的饭菜过来,就算是过节。
大门出不了几次。
更谈不上买布做衣。
奶奶给我的马甲直到破烂成缕也没加上袖子。
*
我挣脱了关于过往的这场梦魇,在迷离中醒了过来。
其实有些诧异,怎么会梦到那么小的时候。
后来想想,也许是因为担忧殷管家受冻,内心有了牵挂,勾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
天还没有亮,雪还在无声地落着。
我趴在罗汉榻上,身上盖着狐裘,有些冷,整个人蜷成一团,缩在狐裘下面。
老爷逆光站着,正在收拾身上的衣服。
比起我的狼狈,老爷整齐多了,只需要理一下就能恢复绅士的仪态。
一夜荒唐。
老爷的体力好得惊人,我被他颠三倒四弄了好几次,最后是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他却还有精力起身。
茅成文五十五,茅彦人三十四。
我没见过老爷的模样。
想来应该比茅成文年龄差不多,甚至更大一些。
只是老爷保养得极好,就算在黑夜里,他亲我的时候也能感觉到,除了细微的胡茬,并没有太明显的岁月痕迹。
身材也是好得很,没有赘肉,远超其他同龄糟老头。
“醒了?”
老爷察觉我在打量他,拿起身侧的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了我身边,坐在床边,抚摸我的头发。
“旗袍以后只准穿给老爷一个人看,知道吗?再让谁看了去,我就当你的面挖了他的眼。”老爷抚摸着我,就像是摸他宠爱的猫儿。
明明是他的要求,现在全成了我的错。
我想起了那个盲老仆的眼睛,浑身颤了颤。
“明白了,老爷。”
我仰起头温顺地由他抚摸。
“又饿了?老爷没喂饱你?”
他的手缓缓地下来,用拇指隔着我的眼皮,轻轻地拨弄我的眼珠子,我更扬起一些上半身,让他更就手,于是这样的抚摸很快带上了别的意味。
“淼淼这样,老爷可吃不消。”
老爷轻轻笑了一声,说着他自己都不信的胡话,收了手。
“我这些日子还有事,要出一趟陵川。”他缓缓道,“你乖乖地等老爷回来。”
他戴上礼帽,拿起了手边的大衣,已拄着拐杖走到了门口。
我察觉到了一丝松动,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小心翼翼开口:“老爷……”
“还有事?”
“我能不能……能不能剪一下头发。”我问他,“半长不短的……不好看。”
他在门口停顿了一下,然后才道:“让殷涣给你剪,除此之外不准别人碰。”
*
老爷走了。
他的马车由盲老仆驾着离开了外庄,车轮在雪地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我并没有看到这一幕,是殷管家告诉我的。
老爷很有些事物在外地,隔上一段时间就会让老仆驾车出外一些日子。
除了盲老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想不通一个瞎子怎么驾车,但是这也与我无关。
所以昨天在外庄遇见,是完完全全的巧合。
老爷本来就要前一天在外庄歇息,然后顺手用我排解无聊的长夜。
*
天放晴了。
阳光照在雪地里,比昨天晚上更冷一些。
地笼生了,屋子里暖和了起来。
门房差人抬了洗澡水进来让我沐浴,舒舒服服地在木桶里泡了好一会儿,才觉得缓了口气。
有人来给我加热水。
我睁开眼。
是殷涣。
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夹袄,袄子做工精细厚实,看起来很暖和。
还好。
没有冻着他。
我松了口气再从朦胧的热气中去看他,便有了别的念想冒出来。
那夹袄是很好看的,雪白的毛领子翻出来,抵着他棱角分明的下颚,衬着他那张冷峻的脸,别有一番滋味。
殷管家把桶里的热水缓缓从我脚边倒了进来。
暖流顺着小腿蜿蜒而上,舔舐着皮肤。
滋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情绪。
“太太少泡一会儿便起来吧。天冷,不要受风寒。”殷管家提着空桶对我说完就要走。
我想起了早晨老爷离开时的模样,风尘仆仆的,像是要走很长一阵子。
老爷不在家。
可殷管家在,就在我眼前。
我翻身往他的方向游了一步,攀住浴桶的边缘,仰头看他。
今日来的匆忙。
没人料到这场雪。
……不知道这么冷的夜,殷管家有没有挨冻,有没有添衣?
【作者有话说】
上一章谁说的?
不得不承认,老爷似乎真有点绿帽癖?
第20章 老爷不在家
我家五个孩子。
我是老大。
我爹在外面找了份工,早早带着我娘外出讨生活。
我从小是由奶奶抚养大,与父母之间没有多少感情……后来就陆陆续续有了弟妹,奶奶老了,我便养家。
五岁的时候就会做饭,六岁可以上山砍柴。
每年最盼望的事,就是过年的时候能吃上一口肉,穿上一件新衣。可家里太穷,父母说我是老大,便从来不给我裁衣服。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幺弟幺妹是每年都有新衣的。
最早的几年,阿奶还活着,刚入腊月就把一年到头攒的点银子换了花线,接些女工活计,攒一些零钱,赶着腊八前扯一块布料,给我做件衣服。
晚上舍不得点灯。
阿奶就着风雪,在月光下赶工。
她活着的最后一年,已经看不清东西,赶不出多少女工,只能赚得一点点钱,给我做了一件马甲。
除夕那天,阿奶病得重了,躺在床上,把那件马甲让我穿上。
她眯着眼笑着说:“我们家淼淼是真好看,像是大户人家的少爷。”
“等开春奶奶病好了,再给你加袖子。”她又说。
可她没等到春天。
我也没有。
初一早晨她便咽了气,初二的时候,我爹用我换了一袋米,还有一块肉。
锅里肉刚炖烂的时候,我就被人牙子带走,卖入了香旖院。
又被茅成文看上,养在了后宅。
从此,穿上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只是这些衣服最后都没什么好下场,撕开的,被揉皱的,成了浪荡的注脚。
而春节……
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春节的。
茅家大太太对我们管教严苛,身上没有一分余钱。
茅成文和他的妻妾们团年后,会送一份冷掉的饭菜过来,就算是过节。
大门出不了几次。
更谈不上买布做衣。
奶奶给我的马甲直到破烂成缕也没加上袖子。
*
我挣脱了关于过往的这场梦魇,在迷离中醒了过来。
其实有些诧异,怎么会梦到那么小的时候。
后来想想,也许是因为担忧殷管家受冻,内心有了牵挂,勾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
天还没有亮,雪还在无声地落着。
我趴在罗汉榻上,身上盖着狐裘,有些冷,整个人蜷成一团,缩在狐裘下面。
老爷逆光站着,正在收拾身上的衣服。
比起我的狼狈,老爷整齐多了,只需要理一下就能恢复绅士的仪态。
一夜荒唐。
老爷的体力好得惊人,我被他颠三倒四弄了好几次,最后是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他却还有精力起身。
茅成文五十五,茅彦人三十四。
我没见过老爷的模样。
想来应该比茅成文年龄差不多,甚至更大一些。
只是老爷保养得极好,就算在黑夜里,他亲我的时候也能感觉到,除了细微的胡茬,并没有太明显的岁月痕迹。
身材也是好得很,没有赘肉,远超其他同龄糟老头。
“醒了?”
老爷察觉我在打量他,拿起身侧的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了我身边,坐在床边,抚摸我的头发。
“旗袍以后只准穿给老爷一个人看,知道吗?再让谁看了去,我就当你的面挖了他的眼。”老爷抚摸着我,就像是摸他宠爱的猫儿。
明明是他的要求,现在全成了我的错。
我想起了那个盲老仆的眼睛,浑身颤了颤。
“明白了,老爷。”
我仰起头温顺地由他抚摸。
“又饿了?老爷没喂饱你?”
他的手缓缓地下来,用拇指隔着我的眼皮,轻轻地拨弄我的眼珠子,我更扬起一些上半身,让他更就手,于是这样的抚摸很快带上了别的意味。
“淼淼这样,老爷可吃不消。”
老爷轻轻笑了一声,说着他自己都不信的胡话,收了手。
“我这些日子还有事,要出一趟陵川。”他缓缓道,“你乖乖地等老爷回来。”
他戴上礼帽,拿起了手边的大衣,已拄着拐杖走到了门口。
我察觉到了一丝松动,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小心翼翼开口:“老爷……”
“还有事?”
“我能不能……能不能剪一下头发。”我问他,“半长不短的……不好看。”
他在门口停顿了一下,然后才道:“让殷涣给你剪,除此之外不准别人碰。”
*
老爷走了。
他的马车由盲老仆驾着离开了外庄,车轮在雪地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我并没有看到这一幕,是殷管家告诉我的。
老爷很有些事物在外地,隔上一段时间就会让老仆驾车出外一些日子。
除了盲老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想不通一个瞎子怎么驾车,但是这也与我无关。
所以昨天在外庄遇见,是完完全全的巧合。
老爷本来就要前一天在外庄歇息,然后顺手用我排解无聊的长夜。
*
天放晴了。
阳光照在雪地里,比昨天晚上更冷一些。
地笼生了,屋子里暖和了起来。
门房差人抬了洗澡水进来让我沐浴,舒舒服服地在木桶里泡了好一会儿,才觉得缓了口气。
有人来给我加热水。
我睁开眼。
是殷涣。
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夹袄,袄子做工精细厚实,看起来很暖和。
还好。
没有冻着他。
我松了口气再从朦胧的热气中去看他,便有了别的念想冒出来。
那夹袄是很好看的,雪白的毛领子翻出来,抵着他棱角分明的下颚,衬着他那张冷峻的脸,别有一番滋味。
殷管家把桶里的热水缓缓从我脚边倒了进来。
暖流顺着小腿蜿蜒而上,舔舐着皮肤。
滋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情绪。
“太太少泡一会儿便起来吧。天冷,不要受风寒。”殷管家提着空桶对我说完就要走。
我想起了早晨老爷离开时的模样,风尘仆仆的,像是要走很长一阵子。
老爷不在家。
可殷管家在,就在我眼前。
我翻身往他的方向游了一步,攀住浴桶的边缘,仰头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