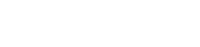等船抵达对岸,送葬队也出现在河边,陈大郎和陈二郎没有交谈,却默契地停下脚步不走了。
杜悯挥手示意衙役先离去,他负手而立,静静地望着这一出好戏。
孟青看向河面,一个月过去,水位又降了, 黄河即将进入枯水期。
“对岸发生什么事了?”陈二郎问。
“河清县和河阴县打压厚葬之风,什么身份用多少陪葬品,都要合乎律令,违制的陪葬品都要被扣下。”杜悯解释,“这个送葬队看来是外地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被扣下了。”
“外地的送葬队?他们把亡父亡母葬于北邙山,日后岂不是不能年年亲自前来祭拜?”陈二郎又问。
“你待会儿问问他们。”杜悯暗笑。
一柱香后,面带愠色的送葬队乘船过来,陈大郎和陈二郎都上前帮忙抬棺,主家上前感谢,两方攀谈上,陈二郎问起他的疑问。
“坟墓立在此地,牌位供在家里,在牌位前祭拜就可。”主家回答。
“可尸骨不入祖坟,我心里总是不安,恐日夜惦记。”陈二郎说。
“我死后也要来此地的。”主人家解释一句。
陈二郎明白了,这是打算迁移祖坟。
“二嫂,你可看明白了?接下来的发展可就不由我了,别说我欺人太甚。”杜悯走到孟青身边嘀咕。
“他的死还没让你消气?”孟青反问,“这就是两个贪心重的无能之辈,何必勾起他们的贪欲?戏耍这样的人,也能让你痛快?”
“二嫂,打压你、戏耍你、得罪过你的人,是不是只要他死了,他做下的恶就能一笔勾销?人死债消?”杜悯正色道。
“师弟,可以走了。”陈大郎喊。
杜悯指送葬队,示意他们先跟着走。
陈大郎巴不得,他拽走陈二郎,打算趁机商量一下是否迁坟。
“我在阻止你,你看不出我的态度?”孟青问。
杜悯点点头,“也对,我爹忘恩负义,利用你又想毁了你,你还一心帮助他儿子,是个善人。”
孟青沉默,她不是善人,她在七年前被赐予一场惊梦,两年后,她把罪魁祸首的儿子抢了过来,占为己有。
“换成我,我一定在自己得到想要的东西之后,毁了他。”杜悯屈指指向自己,“二嫂,我就是这样的人。陈明章施加在我身上的种种,我记忆犹新,他栽在我手上是他的报应。”
“好吧。”孟青认同地点头,“你说得对,人死债消意味着自己的利益受损了,说出去是好听,其中的难受只有自己明白。”
杜悯探究地盯她两眼,发现她是认真的,他大为惊喜,“孺子可教也!”
孟青环顾一圈,可能碍于杜悯身上的官袍和他的名声,附近没什么人,她直言道:“他的死,你出了一份力,这是你自己报了仇销了债吧?”
杜悯反驳不了。
“老三,你今天的行为不是在收债,是在作恶。你二哥在吴县的时候曾跟我转述,你跟他说过一句话,你说你倒要看看,你这个不孝之子会不会成为一个奸臣腐吏。你还记得吗?”孟青问。
杜悯有印象,这句话是他跟杜黎在州府学谈心时说的。
“你曾经厌恶你身上有你爹娘的影子,如今就不怕以后会成为一个你曾经恐惧的样子?”孟青又问。
“有这么严重吗?”杜悯干笑一声。
孟青没回答。
杜悯扭过头吐两口气,他嘴硬道:“就一点小事罢了。”
丧乐声已经听不见了,孟青不再跟他啰嗦,她追了上去。
杜悯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他抬腿跟了上去。
叔嫂俩一前一后快步赶路,最终在义塾门前追上了陈家兄弟俩。
“我们遇到的那个送葬队,去义塾买纸扎明器了。”陈大郎跟杜悯搭话。
“我也给陈大人烧了不少纸扎明器过去。”杜悯说,“看见那个铺面了吗?他家生意好,算卦也准,你们去卜个起坟的日子。”
“不起坟了,不打扰我爹的清净。”陈大郎面带不自在,“我跟我二弟商量好了,就让我爹葬在北邙山吧。”
“北邙山上少闲土,坟墓有成千上万座,朝堂上的官员才多少个?”孟青开口,“你们不要听信风水师的话,据我所知,北邙山上至少埋了三个朝代的王公贵族,甚至有诸侯的墓,可什么北魏南齐,不都倒台了,灭了他们的隋朝都灭亡了。可见风水师的话不靠谱,与其指望死人,不如指望活人。”
杜悯点头,“我二嫂说的也在理,我家往上数三代,祖宗的坟都被夷平了,我不还是当上官了。”
陈二郎看向他,这人到底想怎么样?一会儿一个态度。
“陈大人的墓里没有陪葬品。”杜悯自己惹的祸自己解决,他做出决断:“你俩还是起坟抬棺回乡重新安葬吧。”
“我去卜日子。”陈二郎没脸拒绝,只能抬脚离开。
陈大郎挠挠脸,也跟着去了。
孟青哼一声,事情解决,她去义塾查账。
杜悯看她走远,他摊手也哼一声。
一柱香后,陈家兄弟俩过来了,“风水师说九日后适合起坟移棺。”
杜悯好人做到底,带他们上山认坟墓,并交代道:“你俩身上有重孝,不要往我的官署去,别把我老爹老娘冲撞没了,山下有客栈,你俩就住在这儿。这几天把起坟抬棺的人手找齐,运送棺椁的车驾也备好,最好一个人留在这儿,一个人回洛阳找愿意运送棺椁的船。”
陈大郎和陈二郎对视一眼,二人面露难色,这一通打点下来,他们带来的钱可不够用。
杜悯没了作恶的心,也没了精神,为顾全脸面,他把二人领上山找到陈明章的墓碑,之后下山忙他自己的事去了,再不过问。
孟青在义塾里看了一天的账,到了傍晚,跟她爹娘一起坐船回河清县。
“这一个月,杜悯收缴来的违制陪葬品卖了一千一百多贯,还挺赚钱。”过了河,孟母说,“我听说下个月要建桥了,杜悯还打算在桥头立个碑,感谢送来违制陪葬品的人。”
孟青:“……真够损的。”
孟母哈哈一笑,“河清县的百姓挺乐呵,我经常听人说起这事。”
孟青看见杜黎了,看他裤腿上有泥,问:“你去看稻田了?稻子长势如何?能收了吧?”
“还得大半个月才能全黄。”杜黎回答,“爹,娘,又半个月没见你们了,身子如何?没有不舒服吧?”
“除了想望舟,没有不舒服的。”孟母说。
“就不想我?”孟青斜眼。
“想想想想!想你想得吃不下饭。”孟父笑出声,“这次回来能待几天?”
“能多待几天。”孟青打算这趟回来买下染坊和竹坊,把事情处理利索了再走。回去的路上,她跟孟父孟母讲她和孟春的规划,一路说到兴教坊,晚上也直接住在这儿。
杜悯在官署里等了又等也没等到人回来,他气得提上菜找去兴教坊。
*
“谁啊?”杜黎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拿着筷子就出来了。
“我!”杜悯又重重拍一下门。
杜黎去开门,“你怎么来了?”
杜悯冷笑一声,“呦!已经吃上了?”
“阴阳怪气什么?”杜黎拉他进来,“你提的是什么?食盒?这儿又不是没菜,你还带什么菜?”
杜悯气得杵他一拳,“你给我闭嘴吧!”
杜黎哈哈一笑,他反手闩上门,扬声喊:“爹,娘,我家老三来了。”
孟父孟母迎出来,杜悯收敛了怨气,说:“我在官署等我兄嫂回去吃饭,天都等黑了,也没等到人。”
孟父:“……”
“他俩来我们这儿了。”孟母干巴巴地接一句,“忘记喊你来了。”
“所以我自己找上门了。”杜悯提起手上的食盒,“我还自带了菜。”
孟父孟母不知道如何接话了。
“走,进去吃饭。”杜黎接过食盒。
“杜大人,恕不远迎啊。”孟青见人进来,她笑着恭维一句。
“不请自来,打扰了。”杜悯阴阳怪气,“你俩来这儿吃饭,也不回去说一声。”
“这还用说,没回官署就是来这儿了。”孟青把盛的粥递给他,“现在跟你说一声,这几天我跟你二哥就住在我爹娘这儿,不去官署。”
“回来待几天?”杜悯问。
“五六天吧。”孟青在饭桌上又说一遍她打算以孟春的名义开染坊和竹坊的打算,“跟在洛阳一样,染坊和竹坊的工人由衙门安排,只要手脚是利落的,不管是乞丐还是聋哑人,都能送进去干活儿。”
杜悯听出话外音,“跟洛阳一样?你是走一方造福一方县令啊!”
“看在你的面子上,照顾照顾你岳父。”孟青大言不惭。
“吃饱了?”杜黎拿走孟青手里的筷子,“我去洗碗,你要不要喝水?”
“不喝,吃了粥不喝水。”孟青想消消食,说:“你洗了碗,我们走路送三弟回去。”
“行。”杜黎点头。
被这一打岔,杜悯也忘了他要说什么。
“过几天你要不要跟我们去洛阳?该提亲了。”孟青问。
杜悯点头,“我顺带把望舟接回来,官署里就我一个人住,实在是空荡。”
“等你娶了媳妇,再生了孩子,屋里就热闹了。”孟母接话。
杜悯笑笑,“对,到时候我也有关心我的人了。”
过了一会儿,杜黎提着灯笼出来,“走,我们送你回去。”
“你们跟我过去,直接睡在官署算了,免得又倒腾过来。”杜悯趁机说。
“去吧去吧,不用回来了。”孟母受不了了,这比孟春还粘人,她实在不能理解。
杜黎和孟青拿着换洗衣裳跟杜悯走了。
杜悯顿时浑身舒畅。
走在路上,杜悯袒露他打算从今年开始,让役夫挖泥沙砌高堤防的打算,“往下清理黄河淤泥的法子作用不大,不如往上拉高高度,变相加深河渠的深度,来年丰水季,堤防能拦更多的水,就不会再发生水患。”
孟青想到记忆里的大堰渠,提议说:“堤防不要直着砌,砌成斜坡,估计会更坚固。”
杜悯想了想,说:“是会更坚固,斜坡的堤防厚度更厚。”
“可以内外都砌斜坡,外斜坡还能用来种庄稼。”杜黎也给出建议。
杜悯挥手示意衙役先离去,他负手而立,静静地望着这一出好戏。
孟青看向河面,一个月过去,水位又降了, 黄河即将进入枯水期。
“对岸发生什么事了?”陈二郎问。
“河清县和河阴县打压厚葬之风,什么身份用多少陪葬品,都要合乎律令,违制的陪葬品都要被扣下。”杜悯解释,“这个送葬队看来是外地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被扣下了。”
“外地的送葬队?他们把亡父亡母葬于北邙山,日后岂不是不能年年亲自前来祭拜?”陈二郎又问。
“你待会儿问问他们。”杜悯暗笑。
一柱香后,面带愠色的送葬队乘船过来,陈大郎和陈二郎都上前帮忙抬棺,主家上前感谢,两方攀谈上,陈二郎问起他的疑问。
“坟墓立在此地,牌位供在家里,在牌位前祭拜就可。”主家回答。
“可尸骨不入祖坟,我心里总是不安,恐日夜惦记。”陈二郎说。
“我死后也要来此地的。”主人家解释一句。
陈二郎明白了,这是打算迁移祖坟。
“二嫂,你可看明白了?接下来的发展可就不由我了,别说我欺人太甚。”杜悯走到孟青身边嘀咕。
“他的死还没让你消气?”孟青反问,“这就是两个贪心重的无能之辈,何必勾起他们的贪欲?戏耍这样的人,也能让你痛快?”
“二嫂,打压你、戏耍你、得罪过你的人,是不是只要他死了,他做下的恶就能一笔勾销?人死债消?”杜悯正色道。
“师弟,可以走了。”陈大郎喊。
杜悯指送葬队,示意他们先跟着走。
陈大郎巴不得,他拽走陈二郎,打算趁机商量一下是否迁坟。
“我在阻止你,你看不出我的态度?”孟青问。
杜悯点点头,“也对,我爹忘恩负义,利用你又想毁了你,你还一心帮助他儿子,是个善人。”
孟青沉默,她不是善人,她在七年前被赐予一场惊梦,两年后,她把罪魁祸首的儿子抢了过来,占为己有。
“换成我,我一定在自己得到想要的东西之后,毁了他。”杜悯屈指指向自己,“二嫂,我就是这样的人。陈明章施加在我身上的种种,我记忆犹新,他栽在我手上是他的报应。”
“好吧。”孟青认同地点头,“你说得对,人死债消意味着自己的利益受损了,说出去是好听,其中的难受只有自己明白。”
杜悯探究地盯她两眼,发现她是认真的,他大为惊喜,“孺子可教也!”
孟青环顾一圈,可能碍于杜悯身上的官袍和他的名声,附近没什么人,她直言道:“他的死,你出了一份力,这是你自己报了仇销了债吧?”
杜悯反驳不了。
“老三,你今天的行为不是在收债,是在作恶。你二哥在吴县的时候曾跟我转述,你跟他说过一句话,你说你倒要看看,你这个不孝之子会不会成为一个奸臣腐吏。你还记得吗?”孟青问。
杜悯有印象,这句话是他跟杜黎在州府学谈心时说的。
“你曾经厌恶你身上有你爹娘的影子,如今就不怕以后会成为一个你曾经恐惧的样子?”孟青又问。
“有这么严重吗?”杜悯干笑一声。
孟青没回答。
杜悯扭过头吐两口气,他嘴硬道:“就一点小事罢了。”
丧乐声已经听不见了,孟青不再跟他啰嗦,她追了上去。
杜悯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他抬腿跟了上去。
叔嫂俩一前一后快步赶路,最终在义塾门前追上了陈家兄弟俩。
“我们遇到的那个送葬队,去义塾买纸扎明器了。”陈大郎跟杜悯搭话。
“我也给陈大人烧了不少纸扎明器过去。”杜悯说,“看见那个铺面了吗?他家生意好,算卦也准,你们去卜个起坟的日子。”
“不起坟了,不打扰我爹的清净。”陈大郎面带不自在,“我跟我二弟商量好了,就让我爹葬在北邙山吧。”
“北邙山上少闲土,坟墓有成千上万座,朝堂上的官员才多少个?”孟青开口,“你们不要听信风水师的话,据我所知,北邙山上至少埋了三个朝代的王公贵族,甚至有诸侯的墓,可什么北魏南齐,不都倒台了,灭了他们的隋朝都灭亡了。可见风水师的话不靠谱,与其指望死人,不如指望活人。”
杜悯点头,“我二嫂说的也在理,我家往上数三代,祖宗的坟都被夷平了,我不还是当上官了。”
陈二郎看向他,这人到底想怎么样?一会儿一个态度。
“陈大人的墓里没有陪葬品。”杜悯自己惹的祸自己解决,他做出决断:“你俩还是起坟抬棺回乡重新安葬吧。”
“我去卜日子。”陈二郎没脸拒绝,只能抬脚离开。
陈大郎挠挠脸,也跟着去了。
孟青哼一声,事情解决,她去义塾查账。
杜悯看她走远,他摊手也哼一声。
一柱香后,陈家兄弟俩过来了,“风水师说九日后适合起坟移棺。”
杜悯好人做到底,带他们上山认坟墓,并交代道:“你俩身上有重孝,不要往我的官署去,别把我老爹老娘冲撞没了,山下有客栈,你俩就住在这儿。这几天把起坟抬棺的人手找齐,运送棺椁的车驾也备好,最好一个人留在这儿,一个人回洛阳找愿意运送棺椁的船。”
陈大郎和陈二郎对视一眼,二人面露难色,这一通打点下来,他们带来的钱可不够用。
杜悯没了作恶的心,也没了精神,为顾全脸面,他把二人领上山找到陈明章的墓碑,之后下山忙他自己的事去了,再不过问。
孟青在义塾里看了一天的账,到了傍晚,跟她爹娘一起坐船回河清县。
“这一个月,杜悯收缴来的违制陪葬品卖了一千一百多贯,还挺赚钱。”过了河,孟母说,“我听说下个月要建桥了,杜悯还打算在桥头立个碑,感谢送来违制陪葬品的人。”
孟青:“……真够损的。”
孟母哈哈一笑,“河清县的百姓挺乐呵,我经常听人说起这事。”
孟青看见杜黎了,看他裤腿上有泥,问:“你去看稻田了?稻子长势如何?能收了吧?”
“还得大半个月才能全黄。”杜黎回答,“爹,娘,又半个月没见你们了,身子如何?没有不舒服吧?”
“除了想望舟,没有不舒服的。”孟母说。
“就不想我?”孟青斜眼。
“想想想想!想你想得吃不下饭。”孟父笑出声,“这次回来能待几天?”
“能多待几天。”孟青打算这趟回来买下染坊和竹坊,把事情处理利索了再走。回去的路上,她跟孟父孟母讲她和孟春的规划,一路说到兴教坊,晚上也直接住在这儿。
杜悯在官署里等了又等也没等到人回来,他气得提上菜找去兴教坊。
*
“谁啊?”杜黎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拿着筷子就出来了。
“我!”杜悯又重重拍一下门。
杜黎去开门,“你怎么来了?”
杜悯冷笑一声,“呦!已经吃上了?”
“阴阳怪气什么?”杜黎拉他进来,“你提的是什么?食盒?这儿又不是没菜,你还带什么菜?”
杜悯气得杵他一拳,“你给我闭嘴吧!”
杜黎哈哈一笑,他反手闩上门,扬声喊:“爹,娘,我家老三来了。”
孟父孟母迎出来,杜悯收敛了怨气,说:“我在官署等我兄嫂回去吃饭,天都等黑了,也没等到人。”
孟父:“……”
“他俩来我们这儿了。”孟母干巴巴地接一句,“忘记喊你来了。”
“所以我自己找上门了。”杜悯提起手上的食盒,“我还自带了菜。”
孟父孟母不知道如何接话了。
“走,进去吃饭。”杜黎接过食盒。
“杜大人,恕不远迎啊。”孟青见人进来,她笑着恭维一句。
“不请自来,打扰了。”杜悯阴阳怪气,“你俩来这儿吃饭,也不回去说一声。”
“这还用说,没回官署就是来这儿了。”孟青把盛的粥递给他,“现在跟你说一声,这几天我跟你二哥就住在我爹娘这儿,不去官署。”
“回来待几天?”杜悯问。
“五六天吧。”孟青在饭桌上又说一遍她打算以孟春的名义开染坊和竹坊的打算,“跟在洛阳一样,染坊和竹坊的工人由衙门安排,只要手脚是利落的,不管是乞丐还是聋哑人,都能送进去干活儿。”
杜悯听出话外音,“跟洛阳一样?你是走一方造福一方县令啊!”
“看在你的面子上,照顾照顾你岳父。”孟青大言不惭。
“吃饱了?”杜黎拿走孟青手里的筷子,“我去洗碗,你要不要喝水?”
“不喝,吃了粥不喝水。”孟青想消消食,说:“你洗了碗,我们走路送三弟回去。”
“行。”杜黎点头。
被这一打岔,杜悯也忘了他要说什么。
“过几天你要不要跟我们去洛阳?该提亲了。”孟青问。
杜悯点头,“我顺带把望舟接回来,官署里就我一个人住,实在是空荡。”
“等你娶了媳妇,再生了孩子,屋里就热闹了。”孟母接话。
杜悯笑笑,“对,到时候我也有关心我的人了。”
过了一会儿,杜黎提着灯笼出来,“走,我们送你回去。”
“你们跟我过去,直接睡在官署算了,免得又倒腾过来。”杜悯趁机说。
“去吧去吧,不用回来了。”孟母受不了了,这比孟春还粘人,她实在不能理解。
杜黎和孟青拿着换洗衣裳跟杜悯走了。
杜悯顿时浑身舒畅。
走在路上,杜悯袒露他打算从今年开始,让役夫挖泥沙砌高堤防的打算,“往下清理黄河淤泥的法子作用不大,不如往上拉高高度,变相加深河渠的深度,来年丰水季,堤防能拦更多的水,就不会再发生水患。”
孟青想到记忆里的大堰渠,提议说:“堤防不要直着砌,砌成斜坡,估计会更坚固。”
杜悯想了想,说:“是会更坚固,斜坡的堤防厚度更厚。”
“可以内外都砌斜坡,外斜坡还能用来种庄稼。”杜黎也给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