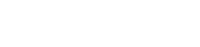林青青挠了挠头,露出一个有些憨厚的笑容:“我不太会,你随便听听哈。”
说着,她举起恋人牌,讲解得有些磕磕绊绊:“这个,这个是不是说明你最近有桃花啊?这个牌的正位象征着爱情、浪漫、灵魂伴侣什么的。”
我挑了挑眉,又不受控制地想起铅色的头发。
她们凑过来看这张牌,发出类似起哄的声音,戏谑着、互相推搡着,开始和我细细数着哪几个男生早就暗恋我,推测谁最有可能是这张恋人牌指向的对象。
气氛从刚刚有些生疏的紧凑转变为了心照不宣的欢愉。好像一旦沾染上性缘,我才会蜕去一层被她们赋予的看似仰望实则贬损的光环,成为正常人类的一员。
“那这张呢?”我装作很有兴趣地样子拿起女皇牌,企图让她们停止将我和一些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人配对。
林青青从一旁拿出一本像说明书一样的东西,快速翻动着书页:“这张,大概是指你会很有创造力,收获一些成果。”
这张牌没有让她们丧失对刚刚话题的兴趣,李逸岚催促着林青青多说一点,试图把女皇牌也与我即将到来的恋情挂上钩。
林青青被催得急了,翻书的动作变得有些粗暴,书页在她手中哗哗作响。我抬头望着头顶的那颗郁郁葱葱的大树,把翻动书页的声音想象成风吹动叶子的声音,好让心中的燥热减轻一些。
“翻到了翻到了,”林青青轻轻扯了扯我的衣角,让我不要走神:“丰饶、自然、生机、家庭美满、母爱……”
喉咙里涌现出血液的味道,我知道自己没办法再听下去了。
如果可以,就让那张死神牌杀掉此刻的我吧。
“倪阳,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苍白。”一个女生发出惊呼,扶住了我的肩膀。
我张口想要说话,但嗓子没有声音,嘴巴只是徒劳地张开又闭合。
李逸岚起身大叫着“有人中暑了”,然后沿着树荫一路小跑,问有没有人带了藿香正气水。
林青青捏着那张死神牌,有些神叨叨地问身边的人:“我现在把这张牌撕了,倪阳是不是就好了?”
没有人理她。
我又听到了书页翻动的声音,但这次有微微的风拂过我的脸。我睁大眼睛,发觉是一阵风吹动了叶子。
我思考着为什么自己不抬头就看见了树叶被吹动,脑子像是卡了带,意识不到自己已经仰面倒在了地上。
后面的事情我记不太清了,等我醒过来时,眼前不再是大片飘动的绿色,而是医务室有些发黄的屋顶。
那天我也是这样躺在一张干瘪的小床上,后背被硌得生疼。
也是一样视线模糊,听不清除了自己的心跳和呼吸之外的声音。
我一瞬间有些晃神,分不清时间到底有没有流逝掉两年。
我耸动鼻子,没有闻到空气里潮湿发霉的气味,而是清爽的、混杂着隐隐的消毒水味道的干燥空气。
不再是那个阴雨连绵的城市。
意识到之后,我感受到紧绷着的身体微微放松了下来,但心脏仍是一阵阵的刺痛。
我蜷缩着,眼泪流过指缝,砸进皱巴巴的无菌床单。
头痛欲裂,四肢传来撕裂般的疼痛,我在被名为痛苦的隐形巨兽啃咬着,分食着,咀嚼着。
突然,我好像听到了轻轻的吉他声。
我压制住啜泣的声音,害怕那片薄薄的帘子后面是一个熟悉的人,来撞破我的失态。
一个女生安静地哼唱着,声音有些沙哑,又带着少年独有的清脆,淡淡地把旋律从舌尖和唇齿间吞吐出来。
“我太懂得,
抓住这一刻就不会再失落,
遗失掉自我。
而你就在此刻,
就在这里,
找到我。”
医务室的窗子是打开的,一阵阵的微风从窗户的缝隙处吹来,帘子被风轻轻撩起一个角。
我看到了一双蓝白色的鞋子。
“同学,头都撞出包了就不要弹吉他了,旁边还有同学在休息!”
急促而尖锐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是医务室坐诊的徐医生回来了。
她匆忙放下吉他,吉他撞到床上发出沉闷的声音。
“可是我的头好痛,弹一下吉他可以转移注意力嘛。”她笑嘻嘻地回话,声线跟刚才那个有些忧郁的声音大相径庭。
徐医生没好气地赶人:“没什么事了就快走,我第一次见开学第一天头撞门上撞出包的。”
“我也是第一次见那么透明的门。”
她的话把徐老师逗笑了,语气温和地催着她回教室。
她好像也从来不知道自己有着随便说上几句话就能让人喜欢上她的能力。
我继续蜷缩着,听到几道杂乱的脚步声,猜测着医务室此刻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的眼睛被泪水糊住而无法睁开,头部的沉痛又让我想要继续昏睡。
意识朦胧间,我听到了时驰夕的声音。
“你需要我在这里陪你吗?”
她的身影透过白色的帘子,影影绰绰地撞进我的视线里。
沉默了许久,我听到自己说:
“嗯。”
时驰夕的吉他弹得很好,顺畅悠扬,不轻不重,刚好盖住我不再收束的哭声。
所以说,我讨厌时驰夕。
第10章 游戏
医务室的事情发生之后,每当时驰夕一出现在我的周围,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四个大字:自乱阵脚。
我深深地恐惧时驰夕知道那个在医务室床上啜泣、痛哭的人是我,恐惧她把这件事情无关痛痒地说给朋友听,然后话题再次像蒲公英一般被吹散,落在众人耳中。
我讨厌这种不安定的感觉。
于是几乎是自保一般,我的目光总是忍不住落在她的身上,想要知道她今天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甚至想了什么。
很病态,对吧?
但我毫无办法。
每次在人群中对视,我都会觉得她的目光像一把利剑一般刺穿了我,将我钉死在医务室那张狭窄的小床上。
“时驰夕,你知道吧?”某天,祝如愿在大课间转过身来,把她的手机递到我的面前。
上面是时驰夕那张厌倦一切的脸,戴着一副大大的银色头戴式耳机,穿着宽大到超出正常尺码的校服,依靠在天台边缘的栏杆上,正在用一支打火机点燃一根烟。
我一瞬间紧张到胃部发紧,还要装作不感兴趣地把祝如愿的手机推开,说上一句“不认识”。
赵泽从教室背后绕过来,手里还拿着值日用的扫把:“这照片真装啊。找人偷拍的自己吧?”
祝如愿懒得搭理她,继续朝我推了推手机,食指和中指不断放大那张照片,直至时驰夕的脸占据了整张屏幕。
“多帅啊,多好看啊,”我能感受到她在观察我的表情,这让我更加慌张,“你记忆挺好的,怎么会不认识?”
赵泽一把抢过手机,随意在屏幕上点了两下:“有人发在校园墙上的?我跟你们讲,她完蛋了,咱学校好几个老师都偷偷加过校园墙。”
祝如愿翻了个大大的白眼,跳起来和赵泽抢起了手机,两个人挤作一团,把我桌子上的试卷弄落了一地。
我强压心中的烦躁,一点一点把试卷捡起来。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时驰夕,长得有点像倪阳?”
我的心狠狠一滞,猛地抬起头来,顿时有些头晕目眩。
祝如愿已经抢到了手机,身边围过来几个女生凑在她身边看照片。
某个人起了话头,其余人自然就开始比对起我们的五官。扫视的目光在我脸上涌动,像虫子般让我发痒又作呕。
“鼻子,鼻子很像,都好挺诶,羡慕羡慕。”
“还有嘴巴!不过倪阳嘴巴要厚一点吧,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嘴巴厚的……”
“哪里像了!这人气质跟倪阳完全不一样好吧。”
“是有点像诶,不过倪阳戴着眼镜把眼睛都遮掉了一部分。”
“倪阳,把眼镜摘掉让我们看看嘛!”
她们一定是友善的,是亲切的。
她们是没有恶意的。
我努力挤出平日里最擅长的笑容,手却死死扣住桌子边缘,想要支撑住自己即将坍塌的礼貌。
看着她们开合的嘴巴,我感觉胃正一阵阵反酸。呕欲像潮汐一般击打着我的身体。
祝如愿应该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她大手一挥收起了手机,嚷着自己数学卷子丢了,让我去办公室帮她找一张新的。
我简直是落荒而逃。
等我反应过来时,我已经走到了时驰夕那张照片里正倚靠着的那片围栏。
被她轻靠过的栏杆,上面是斑驳而破碎的青色,像她眼下隐隐的乌青,像她偶尔沙哑的声音。
我灵魂出窍一般摸上去,直到手指传来微微的刺痛感。
令人……讨厌的时驰夕。
说着,她举起恋人牌,讲解得有些磕磕绊绊:“这个,这个是不是说明你最近有桃花啊?这个牌的正位象征着爱情、浪漫、灵魂伴侣什么的。”
我挑了挑眉,又不受控制地想起铅色的头发。
她们凑过来看这张牌,发出类似起哄的声音,戏谑着、互相推搡着,开始和我细细数着哪几个男生早就暗恋我,推测谁最有可能是这张恋人牌指向的对象。
气氛从刚刚有些生疏的紧凑转变为了心照不宣的欢愉。好像一旦沾染上性缘,我才会蜕去一层被她们赋予的看似仰望实则贬损的光环,成为正常人类的一员。
“那这张呢?”我装作很有兴趣地样子拿起女皇牌,企图让她们停止将我和一些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人配对。
林青青从一旁拿出一本像说明书一样的东西,快速翻动着书页:“这张,大概是指你会很有创造力,收获一些成果。”
这张牌没有让她们丧失对刚刚话题的兴趣,李逸岚催促着林青青多说一点,试图把女皇牌也与我即将到来的恋情挂上钩。
林青青被催得急了,翻书的动作变得有些粗暴,书页在她手中哗哗作响。我抬头望着头顶的那颗郁郁葱葱的大树,把翻动书页的声音想象成风吹动叶子的声音,好让心中的燥热减轻一些。
“翻到了翻到了,”林青青轻轻扯了扯我的衣角,让我不要走神:“丰饶、自然、生机、家庭美满、母爱……”
喉咙里涌现出血液的味道,我知道自己没办法再听下去了。
如果可以,就让那张死神牌杀掉此刻的我吧。
“倪阳,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苍白。”一个女生发出惊呼,扶住了我的肩膀。
我张口想要说话,但嗓子没有声音,嘴巴只是徒劳地张开又闭合。
李逸岚起身大叫着“有人中暑了”,然后沿着树荫一路小跑,问有没有人带了藿香正气水。
林青青捏着那张死神牌,有些神叨叨地问身边的人:“我现在把这张牌撕了,倪阳是不是就好了?”
没有人理她。
我又听到了书页翻动的声音,但这次有微微的风拂过我的脸。我睁大眼睛,发觉是一阵风吹动了叶子。
我思考着为什么自己不抬头就看见了树叶被吹动,脑子像是卡了带,意识不到自己已经仰面倒在了地上。
后面的事情我记不太清了,等我醒过来时,眼前不再是大片飘动的绿色,而是医务室有些发黄的屋顶。
那天我也是这样躺在一张干瘪的小床上,后背被硌得生疼。
也是一样视线模糊,听不清除了自己的心跳和呼吸之外的声音。
我一瞬间有些晃神,分不清时间到底有没有流逝掉两年。
我耸动鼻子,没有闻到空气里潮湿发霉的气味,而是清爽的、混杂着隐隐的消毒水味道的干燥空气。
不再是那个阴雨连绵的城市。
意识到之后,我感受到紧绷着的身体微微放松了下来,但心脏仍是一阵阵的刺痛。
我蜷缩着,眼泪流过指缝,砸进皱巴巴的无菌床单。
头痛欲裂,四肢传来撕裂般的疼痛,我在被名为痛苦的隐形巨兽啃咬着,分食着,咀嚼着。
突然,我好像听到了轻轻的吉他声。
我压制住啜泣的声音,害怕那片薄薄的帘子后面是一个熟悉的人,来撞破我的失态。
一个女生安静地哼唱着,声音有些沙哑,又带着少年独有的清脆,淡淡地把旋律从舌尖和唇齿间吞吐出来。
“我太懂得,
抓住这一刻就不会再失落,
遗失掉自我。
而你就在此刻,
就在这里,
找到我。”
医务室的窗子是打开的,一阵阵的微风从窗户的缝隙处吹来,帘子被风轻轻撩起一个角。
我看到了一双蓝白色的鞋子。
“同学,头都撞出包了就不要弹吉他了,旁边还有同学在休息!”
急促而尖锐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是医务室坐诊的徐医生回来了。
她匆忙放下吉他,吉他撞到床上发出沉闷的声音。
“可是我的头好痛,弹一下吉他可以转移注意力嘛。”她笑嘻嘻地回话,声线跟刚才那个有些忧郁的声音大相径庭。
徐医生没好气地赶人:“没什么事了就快走,我第一次见开学第一天头撞门上撞出包的。”
“我也是第一次见那么透明的门。”
她的话把徐老师逗笑了,语气温和地催着她回教室。
她好像也从来不知道自己有着随便说上几句话就能让人喜欢上她的能力。
我继续蜷缩着,听到几道杂乱的脚步声,猜测着医务室此刻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的眼睛被泪水糊住而无法睁开,头部的沉痛又让我想要继续昏睡。
意识朦胧间,我听到了时驰夕的声音。
“你需要我在这里陪你吗?”
她的身影透过白色的帘子,影影绰绰地撞进我的视线里。
沉默了许久,我听到自己说:
“嗯。”
时驰夕的吉他弹得很好,顺畅悠扬,不轻不重,刚好盖住我不再收束的哭声。
所以说,我讨厌时驰夕。
第10章 游戏
医务室的事情发生之后,每当时驰夕一出现在我的周围,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四个大字:自乱阵脚。
我深深地恐惧时驰夕知道那个在医务室床上啜泣、痛哭的人是我,恐惧她把这件事情无关痛痒地说给朋友听,然后话题再次像蒲公英一般被吹散,落在众人耳中。
我讨厌这种不安定的感觉。
于是几乎是自保一般,我的目光总是忍不住落在她的身上,想要知道她今天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甚至想了什么。
很病态,对吧?
但我毫无办法。
每次在人群中对视,我都会觉得她的目光像一把利剑一般刺穿了我,将我钉死在医务室那张狭窄的小床上。
“时驰夕,你知道吧?”某天,祝如愿在大课间转过身来,把她的手机递到我的面前。
上面是时驰夕那张厌倦一切的脸,戴着一副大大的银色头戴式耳机,穿着宽大到超出正常尺码的校服,依靠在天台边缘的栏杆上,正在用一支打火机点燃一根烟。
我一瞬间紧张到胃部发紧,还要装作不感兴趣地把祝如愿的手机推开,说上一句“不认识”。
赵泽从教室背后绕过来,手里还拿着值日用的扫把:“这照片真装啊。找人偷拍的自己吧?”
祝如愿懒得搭理她,继续朝我推了推手机,食指和中指不断放大那张照片,直至时驰夕的脸占据了整张屏幕。
“多帅啊,多好看啊,”我能感受到她在观察我的表情,这让我更加慌张,“你记忆挺好的,怎么会不认识?”
赵泽一把抢过手机,随意在屏幕上点了两下:“有人发在校园墙上的?我跟你们讲,她完蛋了,咱学校好几个老师都偷偷加过校园墙。”
祝如愿翻了个大大的白眼,跳起来和赵泽抢起了手机,两个人挤作一团,把我桌子上的试卷弄落了一地。
我强压心中的烦躁,一点一点把试卷捡起来。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时驰夕,长得有点像倪阳?”
我的心狠狠一滞,猛地抬起头来,顿时有些头晕目眩。
祝如愿已经抢到了手机,身边围过来几个女生凑在她身边看照片。
某个人起了话头,其余人自然就开始比对起我们的五官。扫视的目光在我脸上涌动,像虫子般让我发痒又作呕。
“鼻子,鼻子很像,都好挺诶,羡慕羡慕。”
“还有嘴巴!不过倪阳嘴巴要厚一点吧,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嘴巴厚的……”
“哪里像了!这人气质跟倪阳完全不一样好吧。”
“是有点像诶,不过倪阳戴着眼镜把眼睛都遮掉了一部分。”
“倪阳,把眼镜摘掉让我们看看嘛!”
她们一定是友善的,是亲切的。
她们是没有恶意的。
我努力挤出平日里最擅长的笑容,手却死死扣住桌子边缘,想要支撑住自己即将坍塌的礼貌。
看着她们开合的嘴巴,我感觉胃正一阵阵反酸。呕欲像潮汐一般击打着我的身体。
祝如愿应该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她大手一挥收起了手机,嚷着自己数学卷子丢了,让我去办公室帮她找一张新的。
我简直是落荒而逃。
等我反应过来时,我已经走到了时驰夕那张照片里正倚靠着的那片围栏。
被她轻靠过的栏杆,上面是斑驳而破碎的青色,像她眼下隐隐的乌青,像她偶尔沙哑的声音。
我灵魂出窍一般摸上去,直到手指传来微微的刺痛感。
令人……讨厌的时驰夕。